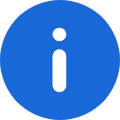暑假到的时候,山里的孩子像干渴的鱼儿遇到了淙淙流淌的清泉。学校刚一宣布放假,我们便得意洋洋地摇晃着脑袋跳出校门,甜丝丝的山风像家长派接我们的姐妹,早早地守候在学校南边的山路上,我们一蹦出校门,就快乐地投入到山风的怀抱里,山风故意怂恿着我们无拘无束地张狂起来。

六月是山野最惬意的季节,蒲公英纷飞的花瓣与蝴蝶比试着谁飞的高,它们像我们的跟屁虫,一直萦绕在我们身边,知了的嗓子亮汪汪的,唱响每个角落,知了们躲在大树枝绿莹莹的叶片下,像怕我们看到它丑陋的样子,它却把嘹亮的无词歌唱得山萌水动,我们踩踢着知了的歌声,被蝴蝶牵引着,被山风推动着,奔向田野,跳向山岗,扑进村前的小河。整整一个夏天,暑假把山沟挤闹得比过年还要热闹几分,无论晨晚,无论晴阴,只要有我们的地方,山沟就灵醒着,山沟就睡不着,大人们在一起时,用饱含希望的目光欣赏着我们的吵闹声,愁苦的日子淹没了大人的快乐,只有我们的吵闹声才能带给他们一丝慰藉,大人们从不讨厌我们的嬉闹,就是仇人家的孩子,大人们也喜欢着,因为我们是大人们的盼想,是山沟的未来,山沟贫困,大人们没有知识、没有文化、没有能力改变穷苦,大人们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
这一年,是个多雨的夏天,见天下雨,大人们说,天上也歉收了,龙王派雨神到地上来收租子的。我们揣着懵懂不解问大人,我们的土地又不是天给的,他们凭什么要来收我们的租子。大人们抬头望着蓝汪汪的天语调无奈地说,地和天是一家子哩,地也是天的,天大地小,天管着地的,地是没有能力违抗天的。大人的话我们依旧似懂非懂,其实大人也是似懂非懂。大人和天一样,是高大的,能管住我们,我们是地,是个小,大人说什么,我们信什么。
每到下午,雷阵雨像有人指挥着似的,一到点儿,准时光顾村庄前的晒场,刚才天还是亮光光的,太阳炸炸的火辣辣的,云白格生生的,云没有隔住的那块天是蓝汪汪的,人要是望着天看去,那种蓝似村上的妇女们用水洗过一样。
村前大晒场上的女人们看守着晒场上黄灿灿的麦子,如看守着收麦天之后所有节日里的白馍或者是香喷喷的大碗面条。男人们下地了,地里还有待收割的麦子,我们是不用下地也不用看守晒麦场的,我们有我们的任务,我们每天的任务是上山挖药,也是在挖我们九月开学时的学费和那个长吊吊冬天的花销,学校的门口有个代销店,那里面摆满了我们童年的所有渴盼。

男人们走了,孩子们走了,妇女们守着晒麦场,担惊受怕似的看着天的脸色,看着看着,天就变脸了。
红彤彤的太阳被妇女们看着看着,就与女人们躲起了猫猫,不见了,白格生生的云彩为村庄撑起了遮阳伞,为天拉起了遮羞布,突然间,一阵恶呆呆的风,从山外呼呼呼地吹来,风夹着青稞味儿,风从村子北边洋蛮坡上路过时,还从裸露的山体上捎带了细细的黄土沬,用人们看不见的手拿着,风漫过村上最好的那块地——油坊坪时,丢掉了手中的黄土沬子,像疯了似的朝着村庄迅猛地扑来,风走过的地里,刚长起来尺余高的玉米苗儿就被人们看不见的风的脚齐茬茬地踩倒了,玉米苗儿像三月三九龙山上敬神的人,见了风,如人见泥塑的神像,虔诚地把腰身躬在地上,头也不敢抬了。
风也是喜欢热闹地方的,风停留在村庄上不走了,风似要人们看到它的威严一般,用它无形的手扯起了村人晒在树枝上花花绿绿的衣服,狠狠地把那些衣服抛向远处,有一些衣服会被风抛到距村庄很远的地方,还有的像元宵节时我们放的孔明灯,飘向天际。有时候,风还会把某户人家圈舍上的木架子推倒,使那些没有意识到它威严的牲口们紧张地嚎叫起来,牲口们一嚎叫,风就更加得意了,又去张牙舞爪地害人。某户人家房檐上的瓦片有时也会被生气的风拽下来抛在地上,摔打成八瓣,风是制造声音的怪物,也像欺负惯了山里人的恶兽,风的嚎叫是惧怕的,夏天的风是不带哨子的,就知道呼呼乱吼。
风一到村庄,村庄上的人和风一样也疯了,所有的人丢弃手头的事,哪怕是炒菜的油锅,也会用水将其浇灭,也许正在解手的女人,提着裤子也会从茅房出来,像疯子一样跑向了晒麦场。晒麦场上晒着一村人的年景,谁也不敢怠慢。妇女们是没有能力能抵挡风的,但谁也不敢麻木不仁,更不能袖手旁观,即使有个人正为孩子哺乳,她也会丢下孩子,任他们去哭。回了家的妇女争先恐后地从每个炊烟笼罩的屋檐下跑向晒麦场,她们要保住白馍白面,如果晒场上的麦子被雨水拿走了,被龙王爷收去了,村庄里的男人们是饶不了她们的。
我们也像疯子一样来了。我们是从山野里跑向晒麦场的。风从山外向山里走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有风来祸害村庄了,我们一行七八个人,看到风的势头,我们相互呼唤着,提了小小的笼子和小尖镢,也像疯子一样,从四面八方的坡上跑向村庄,我们到村庄时,风已经逃跑了,风像一个魔鬼,魔鬼的后面跟着粗壮的雨滴,我们说雨水是天撒下的尿,是风拉下的屎,风走了,就把粪便从天上倒向村庄来祸害我们。
雨大得要命。我们常常如此形容夏天的白雨。雨也是从山外向村庄上走来的,雨像排着队的士兵,在我们还没有看清它们的步伐是否整齐时,雨就齐刷刷地到了村庄,雨滴像从天上掉下来的小石块,将村子里的一切砸出可怕的不同响声,一瞬间,有时我们也说一刹那,雨就笼罩了村庄,看不见天,看不到村庄外的树,黄黄的泥水从坡上、从屋檐后面的洋壕里统统地流向晒麦场。
抢场了。有时,会有女人如此破喉咙大嗓子地喊叫。但更多的时候是来不及喊叫的。所有的人,见到风雨时就会想到抢场。

晒场上的雨滴是斜斜地打在人们的头上和脸上的,像大人的巴掌扇我们的耳光。人是要和雨作斗争的,传说雨是来替龙王收租子的,年年粮食歉收,没有人愿意把粮食交给龙王,人就开始和天和雨和风做斗争,年年如此。晒场上,没有人组织,没有人指挥,没有人分工,黄灿灿的麦秸秆先是被男人们用长把木杈拢起来,男人们挥木杈的动作像战场上与敌人拼刺刀的战士。我们没有木杈的把高,我们就用双臂抱麦秸,大人的木杈像兵器一样从我们身边绕了过去。男人们收拢麦草,女人们持了扫帚从地上扫起被麦糠包裹着的麦粒,雨水已冲了下来,麦粒儿成了焖饭被黄泥包裹着,糊糊的,粘粘的,女人们还是疼怜地扫着,男人把麦草收到哪里,男人的木杈下很快就有了女人的扫帚。
正在我们干得起劲的时候,一个炸雷从天上掉了下来,炸雷落在地上不见了,天上的云却被炸雷炸弹开了,先是一道亮晃晃的霞光从黑恶恶的云缝里伸出手来,霞光是天神的巨手,它一伸出来,就推开了所有的云,云分东西,被天手劈成两半,云分开后,变成了金黄色,大地就亮堂了,天地一清亮,雨就小了,太阳光潮兮兮地照到了晒麦场,雨滴背着一个个小小的太阳,慢悠悠地从空中坠下来,坠下来。
晒麦场上,每个人都成了泥猴,也成了落汤鸡,那些年轻的未结婚的女子,最早地丢弃了木杈或扫帚把,她们怕人们看到他们被雨帖到身上的衣服,怕人们看到她们凸出的胸脯,早早逃离了晒麦场。男人们也丢弃了杈把,他们一边骂着天,一边开始蹲在晒场边抽旱烟,只有女人们气咻咻地一边骂着天一边用簸箕从泥沙中将麦粒移向保管室内的干地上。
太阳又红杠杠地挂了起来,有几片淡黄色的云在太阳底下来回巡逻,雨从那云里像吊挂面一样细细地落下来,落下来。
太阳雨。太阳雨。
不知是谁站在晒麦场喊了一句,我们都抬头去看太阳雨。
有人说太阳雨是太阳的眼泪。
有人问,太阳为什么会流眼泪呢,它的泪是高兴的泪水还是痛苦的泪水。
回答说,太阳流下的是忏悔的泪水。因为我们一向很敬重它,它却躲起来把天空让给风和雨,让风和雨来祸害我们,当它看到我们这么狼狈时,它一定是心疼了,它才流下忏悔的泪水。
晒麦场上的事情交给女人们了。男人们又到地里去扶玉米苗儿了,我们无事可做,大家就相互簇拥着到门前的小河里去清洗身上的泥沙和脏衣服。
我们一边洗一边还在谈论着太阳雨。
有人说太阳雨虽然很坏,但它也有好的一面,它把全村人的心拧到一起了。
有人说将来实现了机械化,就不会有这样的景观了,机械化是不需要大晒场的。
我们说着,打闹着,太阳雨在下着。当男人们回到村庄后,我们顶着太阳雨走向重新升起炊烟的村庄,太阳雨中的村庄像一幅画儿,清丽而宁静,盛装着浓浓的诗意。
秋季开学后没几天,公社团委的几个人来到我们学校,送来了奖状,奖状是鼓励我们的,来人发奖状时指着我们对我们的老师说,这是一群公而忘私的好少年。
我们争先恐后地抢着奖状,想急急地回到村庄去,把消息告诉村庄里的大人们。
回家的路上,我们相互鼓励着,装着成年人的样子,彼此握手,互道祝贺,我们在山路边的石岩上,用小石子刻下一行行为建设山区美好未来的誓言,我们要把自己的青春,奉献给庙岭,我们要用自己学到的知识,用毕生的精力,改变庙岭,使庙岭早日奔跑到共产主义,人们想要什么有什么,要吃肉就会有肉吃,想吃白馍就有白馍,想穿好衣服就有好衣服。
我们看着高远而湛蓝的天,看着翠绿的山,看着泛黄干索的田地,我们渴望秋天再能下一场太阳雨,因为秋天的晒场上也晒着大豆的。
但我们知道,秋天是不会下太阳雨的,秋天只会下连阴雨。

那个夏天,白云记着我们的誓言,蓝天书写着我们的理想,大地见证了我们的行动,庙岭,懂得我们的心思。
秋雨漫长,下了一个多月,世界泡在水中,村庄和村庄外所有的世界全湿透了。地里的粮食全霉了,即将收割的玉米,霉烂在地里,人们骂天,天的脸子平平的,不理人,照旧将冷凄凄的雨洒在庙岭的山水间。小河里积满了灰色的泥水,没有水吃,男人挑着水桶到门前沟垴的石岩下去接矿泉水,接回来的水,还是灰色。没有柴禾烧,男人们将屋里没有用的旧家具用斧头劈了,让女人烧。没有粮食吃,将地里的玉米搬回,煮着吃,像原始人一样。民谚曰,没啥吃,吃挂面,没啥烧,烧架板。
无情的雨,整整下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住在队里的县上干部,回到县上去了,刘队长说,他们再不来了。有人问,那队里有了什么事,怎么办。刘队长没有回答。有人对刘队长说,没有了县上包队干部,你的主心骨就没有了,我们咋办呀。
刘队长笑笑说,有也行,没有也行,人家是人家,咱是咱,没有人家,咱还不吃饭了不成。
大家偷偷笑刘队长。有人说,没有了县上包队干部,才能显出刘队长的威力。
九月中旬,雨住了。
太阳从门前梁上出来了。太阳的热量被雨冲淡了,人们感到太阳用劲照着大地,可大地上还是没有昔日的热量。
刘队长说,公社领导说了,今年是个多雨水的年份,大家一定要有龙口夺食的精神,抢三秋。
有女人打趣问刘队长,什么是三秋呀,明明是一个秋,你却说是三个秋。
刘队长说,三秋你也不知道,秋收,秋种,秋播呀。
伶牙俐齿的女人再问,请问刘队长,秋种和秋播有什么区别。
刘队长想了一会儿说,我也说球不清,反正公社说了,要抢三秋,我们就认作为它是三秋吧。
会计水娃哥说,秋收、秋播,秋管,是三秋。
雨水多,粮食收成就好。这一年,年景丰收了,人们的日子却苦不堪言,收回来的玉米全霉坏了,收回来的大豆,全是坏了。人们吃着发霉的玉米,不是出现肠胃病,就是拉肚子,人人脸上失却气色,庙岭所有的人,像得了团体病,家家户户都有病人,年迈的何先生派上了用场,他天天为人把脉,让儿子去山外小镇为人们抓药。学生上学,连带的馍也没有了。但这一年,也有好处,人们碗里的油水多了,黄豆丰收了,黄豆霉了,做不成杂面,做不成炒面,做不成豆腐,人们就用豆子柞油,经验告诉人们,豆子坏了油不坏。吃了坏豆子油饼,猪不断的死,公社兽医站的兽医,成了庙岭的常客,过去,人们很少知道他们的存在。
正在秋雨下得凶猛的时候,我去了牛湾读完小。
领到新课本不久,国家发生了一件大事。
林彪摔死在内蒙古温都尔汗。那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老师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刘队长也不知道。
有天晚上开会,有个快嘴女人笑着问刘队长,内蒙古温都尔汗在哪里,离咱庙岭有多远。
刘队长说,我不知道。刘队长让我告诉大家,我吓得往队房的门外跑去。
林彪死后没几天,庙岭的老中医也去世了,他是德高望众的何先生。
何先生是庙岭人公认的好大夫,自我懂事起,除了大人叫我们学校的老师为先生外,唯一能被人们称为先生的,就是老中医。
我不知道何先生有什么能耐,被人们尊称为先生,但我知道,除了老师外,还有一种人也可以称作先生,那就是会给人治病的人。
何先生是个医术高超之人,虽然我没有得到过他给予的什么福气,但全队人,都为他披麻戴孝,我也不例外,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死人事件。
何先生的死,是庙岭人最大的损失,也是周边人的损失,更是人们对中药丧失信心的根源,同样是经济损失,健康损失。何先生反对西药,反对化肥,反对农药,惯用中药,为庙岭人的健康做出了贡献。
一个总对人笑的和蔼可亲的老头,没有了呼吸,人们为他穿上新衣服,将他放入棺材,然后将他埋进了黄土坑,这个人从此再见不着了。这就是人死了。我从此认识了死亡。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我总能想起那个老头,那个已经死了的人。许多夜晚,我总在想,我的父母,会不会也有一天像何先生一样,被人埋入黄土坑,想着想着,自己就哭起来。
人们埋了何先生,进入了冬天,雪又来了,长吊吊的,不紧不慢地下。
人们没事做,就想着弄钱过年,鹿池川北部开了八一煤矿,庙岭人,偷偷砍了大腿根粗的松树,背出山门,送到煤窑上做矿柱,换些钱回来。
父亲是一个不敢偷树的人,母亲曾抱怨父亲说,父亲是个连树叶掉下来怕砸伤脑袋的人。不敢偷矿柱,父亲也有挣钱的办法,他领着我二弟上山砍桦梨树的枝条,我们把枝条送到八一煤矿,做窑梢子,也换得钱来。
除此外,父亲还把粗一些的桦梨树,做成劈柴,挑到景村街去卖,有时没有什么可卖,父亲就上山撸松米(冬天的红色松梗),挑到景村街,有时我们也卖椽给山口的盈丰人。
在庙岭,只有三个人卖过松米,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坟沟的何忠有和他弟弟何忠福,也是从这一年开始,父亲买了几十年柴禾,硬是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养育成人。
有个冬天的晚上,我起夜时,不让母亲点煤油灯,自己摸着黑起身小解,父亲问我为什么不让你妈点灯,我只是笑而不语,父亲摸着我身上的隐秘处说,大知道,怕羞了。放心,大给我娃买块布,让你妈给做条短裤。
第二天,父亲又去卖松梗了。那天下雪,父亲挑着松梗去山外赶集,滑倒在大姐家下面的山坡上,大姐夫和他的弟弟将父亲抬了回来。一同来的大姐不住抽我的耳光,她指责我说,碎碎一个娃,穿什么短裤,害什么羞,这山里人,你看谁穿短裤了,就你事多,你现在看,你把大害成这样,年咋过哩。
大姐骂着,却从自己带来的布袋里掏出一块红色的布给了母亲,让母亲给我做了红裤头。
父亲病了很久,亲戚都来探望,我多么希望有人看父亲时,能留下钱给我们,可人们除了带来鸡蛋和挂面,没有一个人送钱来。
看着躺在炕上不能行动的父亲,二姐发狠了,她要做家里的掌柜。她对母亲说,一个父亲倒下了,他还有几个儿女已站起来,有些人,从小没有父亲,不是还照样活在人间,怕啥,我来当家,我就不信,社会主义还能把人饿死。
二姐没有念过多少书,她的豪言壮语,是从住队干部那儿学来的,也是大姐引教的。
二姐领着我和二弟,一起上山砍窑梢子,到了腊月根儿,砍下的窑梢子,堆在门口像埃及的金字塔,黄亮亮,太阳一照,泛出的光耀人眼目。
有一天,太阳红艳艳的,二姐计划让大姐夫帮我们卖掉窑梢子,她早早起来,烙了馍,擀了面条,让我二弟去第二生产队请大姐夫,我和二弟刚走出村庄,发现庙岭头上来了一拨人。
出于好奇,我和二弟站在村路上细细地看着来人。
来人是公社的检查组,他们走进村庄,直奔我家庭院,有一个皮肤白净的男人,直接搬开了我家如山的窑梢子,他拿出一根手腕粗的桦梨树对刘队长说,这家人砍树,你看,砍了多少,这咋行哩,这是明目张胆地破坏集体财产,挖社会主义墙角么。
听来人如此说,我和二弟一时吓傻了,二弟开始尿裤子,他的棉裤在一瞬间,湿了两条腿。
二姐听到了场院人们的说话声,赶忙从院子里出来,阳光照着她整理好的头发和她涂了雪花膏的脸,她跟了大姐多年,知道人情世故,也知道公社人的厉害。她看到公社人后说,原来是你们呀,快进屋,正好,我给我大做了病号饭呢,你们快来吃吧,要不,你看,这天实在是太冷了,做一顿饭实在是不容易。
刘队长急忙走上前去拍了一下二姐的肩膀笑嘻嘻地说,二女子,你把饭做好了,那正好,我还发愁,今日不知道给谁家派饭哩,行,你这女子,早不如巧,那就让领导在你们家吃饭吧,粮票和钱就不要收了,队上会给你们补助粮食的。
二姐一边拍打着胸前的围裙,一边笑呵呵地说,什么话呀,盼都盼不来呢,还收什么粮票呀。现在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县上的干部天天和我大姐在一起,都成了好朋友,我们从来是不收什么粮票的,我们到县上,人家总请我们下馆子哩。
那个年轻的姓张的公社干部丢了手中的一棵树枝,冷了脸子对二姐说,工作就是工作,吃饭就是吃饭,是两回事,你这个女子,可不能搞和平演变呀。
说着,他向身后年龄大的穿着牛皮鞋的人招了手,一同进了我们家庭院。
知道公社干部进了院子,睡在土炕上的父亲故意高声咳咳呆呆地呻吟起来,他想让公社干部去看他,可那两个人并没有走进父亲的旮旯,他们面对二姐端出来的热气腾腾的面条和锅盔,似乎忘记了一切。
很快,他们狼呑虎咽般吃完了,然后抹着嘴走了,走出院子,那个姓张的干部返过身对二姐说,你们家的窑梢子里,有不少树呀,这可不行,那是乱砍滥伐呀。
二姐依旧笑嘻嘻地说,我弟小,不知道啥,我告诉他们,以后不敢胡砍了。
公社人刚走出楼门院子,二姐便开始骂人家。
他对父亲说,大,今日卖不成窑梢子了,我给卖梢子人做的饭,不小心,让猪吃了。
父亲说,你后晌再做,让他们明早天不明就来。
第二天,大姐夫帮我们卖了窑梢子,所得的钱,并没有带回家,大姐夫到书堂山为父亲买了治伤的药。晚上,大姐夫回来时,遭到父亲的指责,嫌他不该把我们好不容易弄下的钱为他买药。
过了冬至后,大姐夫送了钱给母亲,那一年,我们都置办了新衣服。村人羡慕母亲说,还是养女子好,着急时有钱花。
母亲说,养女子好,可人们总希望自家的儿子多。
到了腊月月尽时,公社那个姓张的干部又来了,在我们村上召开批斗会,批斗了许多人,父亲也被批斗了。他咬牙切齿地说,全公社,就你们庙岭队的乱砍乱伐最为严重。他说要弄个人送到监狱里去,做个娃样子,好好治理一下庙岭队的乱砍乱伐。他让社员们指证,谁去合适。社员们茫然了,不知道应该指证谁去。整整开了半天会,也没有定下一个人。那个姓张的说,今日定不下人,晚上就不睡觉,我看你们庙岭的人能还是我们公社人能。
二姐从人群中站了起来,他对那个姓张的说,我去,你不用为难大家了。
社员们把目光紧紧盯在二姐身上。二姐说,我弟的课本上有许多女英雄,我听了他们的故事后,很受感动,所以,我去,我要向女英雄们学习,也不让公社的领导为难。
那个姓张的人走过来用手抖了抖二姐的辫子说,是去坐牢,不是去绣花。
二姐说,我去后,先要告诉国家的人,我们公社有个干部,天天到我们队上寻事,他不是让大家好好抓革命、促生产,而是给社员们寻事。我还要告诉公家的人,那个国家干部,在我们庙岭吃饭,从来不给社员出钱和粮票,他家修房,还让我们队上的社员白白把木椽往他家送,不但不出钱,还不给社员出工钱。
那个姓张的指着二姐气愤地说,你说这些是什么意思?
二姐洋洋得意地摆着头说,举报,你不是要送我们庙岭人进牛王沟吗?我要和你一块进去!在监狱里,我还要和你斗,我就要学女英雄,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有什么不可以。
会开不下去了,社员们的议论声响了起来。
正在此时,公社的书记,一个高个子男人领着一帮人到了会场。他竟然在门外拍起了巴掌。社员们都站了起来,大家都认识公社书记。
看到书记鼓掌,社员们也莫名其妙地鼓掌,社员们的掌声是欢迎书记的。
公社书记走到二姐跟前,拍了她的肩膀说,刘队长,这是一个好苗子呀,要好好培养,为了人民的利益,不顾自己的生死,多么可敬的品格。
那个姓张的干部为书记让了座位,书记坐到正台上,先用目光齐齐地看了每个社员,停了一会儿说,快过年了,来看看大家,还缺少什么,还有哪些困难户,过不了年,公社都要做安排的。至于老张刚才说的,送人进监狱的事,我看先放一放,先过年,但是,有人反映,你们庙岭的乱砍乱伐,的确有问题,要引起注意,知道吗。
掌声又一次响起,掌声响了很久。
过了几天,公社送来了米和面,数量很少,但家家户户都有份儿,从那时起,我们知道,过年没啥吃,有公社管着。公社是一个了不起的机关大院,有时我想,公社那个大院里,是不是住着我们敬爱的党。当然,那个公社书记,也是一个好人,据说,他后来当了很大的官儿。多年后我去鹿池川上学,走出山口,远远的,看到公社白墙的院子,心中就生出敬意。从此,也理解了大姐和二姐,他们为什么总爱唱《公社是棵向阳花》。
【作者简介】:

李虎山 陕西省洛南县人,久居西安,中国作协会员,西部散文学会陕西分会主席,商洛市写作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作家,2021年、2023年陕西省主题创作、陕西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创作作家。曾于北京卫戍区服役,担任过乡镇长,报刊杂志总编。出版长篇小说《鹿池川》《平安》《之间》,中短篇小说集《爱听音乐的狼》,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五十年的眼睛》、长篇报告文学《水润三秦》《庙岭本记》,长篇小说《平安》参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被陕西日报评为读者喜爱的作品并获蒲松龄文学奖,发表作品400万字,获各类文学创作奖50多次。《平安》入围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之间》刚一出版,就赢得读者喜爱。
本期编辑:刘萧姣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