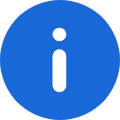不管天上人间,不管贫富贵贱,不管男女老少,皆有生日。
天上神仙我们虽未所见,但据传说他们每逢生日即是笙箫齐奏,鼓乐齐鸣,歌女齐舞,引动天地人神共乐。人间虽然不如天上的神仙,但生日也有无限的乐趣。老人过生日有儿孙环绕膝下,那真有享不尽的天伦之乐;中青年人过生日要邀请亲朋聚会,也有那道不尽的生活乐事。更有那少儿幼童们生日,各个时段都有着不同的喜庆:满岁时有亲朋来庆贺,尽管他们自己不明事理,但长辈却是无限的开心。少儿时稍懂人事,过生日有同龄玩伴们相聚,一个个有耍不尽的纯真童趣……
生日,在天地人间皆是欢喜,为何苍天待我却不是如此?为何夺去了我的生日乐趣?为何给我生日赐予了无限的伤悲?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呀?
早时,我的生日原也是很快乐的。但自从进了五十五岁以后,生日便与思亲、伤愁、悲切这些精神枷锁死死地连接在了一起,一直把我的心情箍得紧紧地、紧紧地……
那是在二零一五年,我带妻子跟着包工的侄儿到了内蒙。我们名义上是帮忙干活,实际是要侄儿带着我们见见世面,顺便在工地混混,这样也能涨一些见识。
我生日那天,天际雾雾沉沉,干风裹着黄沙从早吼到晚。这样的天气既使人寒嗦,也使人沉闷,同时我也隐约地感到有什么不详。都说生日是新年龄段的预兆,这天如果阳光灿烂,新的一年必定是身体健康,诸事如意。如果这天暗晦无日,飞沙走石,新年不是身体有恙,就是家事不顺,抑或仕途一定要进入坎坷。我虽然是唯物主义者,但并不排斥老年人所见的经历之谈。
那天侄子出差去了,晚上妻子见我情绪不畅,为了促我开心,就专意在私人小店买了几个菜,挑了一瓶我时常爱喝的烧酒,拿回放在房东的锅台上,就算给我摆好了过生日的场面。几个菜炒好了以后,我们夫妻二人就对面坐下了,一个当主客,一人相配,饶有兴趣地把我推进了五十五岁的年龄档。
我平常有个习惯,那就是喝酒以后立即就要打瞌睡。而那晚却十分反常,本来喝了过量的烧酒,但是过了半夜却毫无睡意,这是我过后一直解释不清的事。妻子说也许是过生日心情有些激动的缘故,我当时没有附和,没有否定,只是一味地感觉心情游离。我万万没有想到,这游离的心情,就是亲情的牵挂!
过后我才知道,这是冥冥之中神灵给我的信息。就在那晚,我二哥受尽了病痛的折磨,翻来覆去,最后到底没有逃过黑白无常那追命之索,在凌晨三点被带入到了另一个世界!
虽然我和老家相隔几千里,但我和二哥心心相连。他在家一阵阵地难过,我在内蒙一阵阵地心慌;他面对妻儿的陪伴,不停地挣扎于阴阳两界当中,我在内蒙不住地翻来覆去,难以进入梦乡;他在家无奈地痛苦呻吟,我在内蒙不住地唉声叹气……哦,这就是弟兄相念,这就是手足之情啊!

谁人不知手足之重要?谁人不知失去手足之伤痛?我也正是从那天起,每逢生日都要避过众人,抽时间独自坐下来静心地回味往事,思二哥,想二哥,念二哥。当大脑里闪现出他的音容笑貌时,我心里就觉得无限地空落、难过,眼泪一致不住地流淌,身子也不由自主地一阵阵颤抖,一阵阵颤抖……
我们一母同胞共有六人,五儿一女。我大哥接下来是我姐姐,接着是我们四弟兄。宗谱排到我们是登字辈,父亲就给我们取名依次为福、连、成、宪、庚、耀山,我在姊妹排行中是老五。我们弟兄五人自小居住三处,大哥从小就离开老庄,解放前由爷爷领着在原来甘溪区大岭乡柏木垭村居住。至于爷爷为何要这样安排,我小时听婆婆讲:解放初农村要划成份,土地和房产多了就要划成地主。地主成分是被管制和挨斗争的对象,爷爷把大哥引去,土地和家产按照人均就划成了中农,站在了当家做主的阵营,躲过了无休止的批斗。姐姐在二十四岁那年出嫁,最小的耀山幼时出继到了齐姓姨夫家改名荣基,给齐家顶门立户。这样,我们老家就只有二哥和三哥带着我一直驻守前辈们创下的基业。
二哥比三哥大一岁,我却小他十岁,因此在能记事起我就是他俩背上的包袱。那种爬在背上东游西逛的感觉真是无比舒服,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两个哥哥看着我高兴,他们也跟着享受了与同龄人不相同的乐趣,因为像他们这个年龄别人都在在学校课堂读书,接受管束,而不是如他们一样东游西逛,领着小弟玩耍。
我当时年幼,只知道自己耍得痛快,并不明白哥哥们的心事,更不知道他们俩争着背我找乐趣,还有一方面原因是为了想改换一下自己的心境。那时我们家里很穷,尽管一学期学费只有五毛钱,但父母亲还是没办法拿得出。因为经济原因,二哥和三哥头年一同进学堂门,第二年又一起放下书本,回家操起锄头干农活。这是无奈的事,但“穷人的娃子早当家”,我的哥哥们懂事早,尤其是二哥,他在十五六岁时就能干起了成人的活路,生产队很快把它当作全劳(农村在大集体时,那时的生产队也就是现在的村民小组,平常干农活在一起,按照出勤情况记劳动日,年终依照工分进行分配。出勤时把强壮劳力叫全劳力,妇女和老幼叫辅助劳力。全劳工分多,年终分的粮钱多;辅助劳工分少,年终分的粮钱少)。
在二哥十七岁那年,国家修襄渝铁路,动用的主要人力是铁道兵和农民义务工。政策规定修铁路必须抽调各生产队的好劳力,二哥就在那次被大队安排去修路。他上铁路的第二年,市上的一个国有企业要到各县招工人,县上把名额分到各公社,公社又把招工的工作人员介绍到我们大队,叫他自己挑选工人。
从待遇来说,能当上工人那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事:
首先是能转成城镇户口。户口在当时的条件下,农业户口和城镇户口那是天壤之别。农村常年要为口食操不尽的心,想不尽的办法,费不尽的力,能保持常年不断顿就算是富裕家庭了。农业户口的人只有死守在土地上,遇到天时不顺,庄稼歉收,那就只有买返销粮吃,相当大的一部分人,特别是没钱卖粮的特困户和一些不够救济条件的老实人,就只有饿饭一条路。而城镇户口的人,他们都持有“居民粮食供应证”红本子,每人每月国家供应三十斤,细粮(主要指麦子和大米)占60%,粗粮(指玉米大豆一类的粮食)40%,这是政策规定,不用走后门在国有粮站就能买到,天干雨涝一两都少不了。因其户口的差别,农村人自觉地认为比城镇人低一等,教育娃子念书的最理想目标,就是将来能拿上红本本吃粮,这也算是特殊年代社会人员的特殊等级划分吧?
当工人和农民的其次差别体现在安排工作方面 。农村人想参加工作,光明正大的一条路就是考上中专以上的学校被分配,或者有特殊贡献和相当硬的后台,可以挽个圈子安排去工作。考学凭学业成绩,但农村娃子很少能考的上。至于后台之内和其他那些条件,在农村绝大多数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第三是用钱。生产队除开卖给国家的储备粮能换回一点钱以外,一般没有其他方面的来钱路,因而一个工日只能分上一两毛钱。而当上工人以后,每月能按时领工资,虽然不是多么富裕,但日常也不缺钱。
除开以上几条以外,还有身份问题,居住条件优越问题,社会交往问题等等。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工人和农民之间的鸿沟都是无法逾越的。
然而,我二哥当时才进入成年期,思想比较单纯,对人生的宏观把握不住,思维还显得相当幼稚。他受了别人的引诱,自己生出了一念之差,失去了人生中最能改变条件的机会,这些直至在他晚年,我们谈起来都替他感到后悔!
那是招工的老冯到我们队上的时候,适逢二哥从铁路上请假回家。当时由于没有磨面机,吃粮都要用石磨推。中午时分老冯到各家物色人选时,遇到二哥正在推石磨。他看二哥长得壮实,就坐下来交谈。一番言语过后,老冯大喜,急忙去找支部王书记,不容置疑地说要把那个推石磨的小伙子引走。
这下王书记有点着急了,按他最初的心思,招工的来队上给几个老弱人员应付一下就行了,硬劳力要留在生产队干农活。但老冯看了他介绍的几个人都不满意,提出要自己挑选,他当然不敢阻挡。现在既然人家挑到了看中的人,大队不想给也说不过去。他不愧是一个老于世故的人,和老冯打了几句哈哈之过以后主意就来了:
“老冯,你说的那人引不成!”
“那为啥?”老冯有些不解了。
王书记装作为难地说:“人家在铁路上给国家做贡献呢!”
老冯轻松地笑了起来:“这好办,我们给铁路指挥部写一个便函,你们大队重新安排一个人去顶上就行了。”
王书记眼珠转了转,新的点子又来了:“我说的不是那个意思!”
“那你是啥意思?”老冯有些急了。他挑了几天,选了这么一个人,实在不愿意轻易放弃。
“是这么个情况,”王书记一本正经地说:“现在从中央到地方都要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你知道这是宪法规定。任登成在一队,现在一队的队长已经老了,我们要培养他当接班人呢。再说,他家当前也困难,他是主要劳力走不开。”
如果纯粹说家里困难,老冯倒有办法,他能使唤公社帮忙解决这事。但在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的大政策面前,他不敢再和大队争执了。当时这项运动是压倒一切的政治,是政策红线,谁敢碰?他权衡了良久,只好出了个折中意见:“我们再征求一下他自己的意见,好吗?”
“好,那我去问问他!”王书记觉得这是自己稳操胜券的事,毫不犹豫地作了归结。
别过老冯以后,王书记找到我二哥,首先向他摆明了家庭困难的现状,说他一走生产队当然就不会管了。户口一转走,将来想回来那是万难的事。其次,大队已经向公社申报,要把它作为年轻的后备干部作以重点培养,先当生产队长,过几年入党以后当党支部书记。还有,还有……等等。就这样,我二哥,一个十八岁的热血青年,在当地父母官一番“深明大义”的指点以后,又在一顶生产队长的官帽利诱面前动心了。他愉快地听从了王书记的话,拒绝了老冯的好意,在生活中“拨正航向”建家乡,为自己埋下了终生后悔的苦果。
痛心啊……
老冯走后,王书记倒也没有食言,立即向公社申请,要求我二哥当生产队长。公社接到申请,就向铁路干部交涉,要回了二哥,叫他在一队当上了全公社最年轻的生产队长。
这事倒是可喜?还是可叹呐?
二哥那年十八岁。十八岁,叫他管二百多人的生产生活用度,这可是一个不轻的担子啊!生产队长的“官职”要说好听一点是干部,说实在一点就是一个领工头。队长要安排别人干的,自己首先要扑着前面去干。在重活和脏活面前,奸猾的人往往推来让去,这时队长就得抢先干出样子才能捂住他们的嘴。我二哥是天生的公心人,他的信念就是当好干部首先要吃亏。因其如此,他在上任不长的时间,带头苦干,改变了全队出勤效率低的懒惰习惯,赢得了干部和群众普遍的赞誉。
王书记觉得,提拔起来的人在群众当中有了好口碑,这当然是对他这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无形的奖赏,证明了他是当代的伯乐。二哥为他争气,他高兴,于是给二哥帮忙办起了终身大事,也是一般人办不了的事——解决了二哥的终身大事。他运用权术彻底收拢住了二哥的心,两个人也算投桃报李吧!
实际,王德义当时给二哥办的事也是合法的,但当时基层政府就是有法不依,造成了很多家庭的实际困难。
我至今都想不通,那时的公社领导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权利,不,说准确一点是有那么大的胆子。《婚姻法》规定男满二十二岁,女满二十岁就准予结婚。但是公社为了自身的工作好做,借口国家提倡晚婚晚育,硬行将男方年龄推迟到二十五岁,女方推迟到二十三岁。这样,很多青年恋爱之后由于不能及时组成家庭而又分手;还有的单身青年家里过于困难,只好未婚同居。对于未婚同居的现象,公社又组织干部进行处罚,叫去搞义务劳动,或者罚款,这样就人为地造成了社会婚姻的一片混乱。我二哥当时不够晚婚年龄但是够了结婚年龄,王德义就以解决年轻干部家庭困难为理由,向公社领导说情,给他办了结婚手续。没有达到晚婚年龄结婚属于特殊情况,特殊情况如果没有特殊关系公社领导是不能批准的。王书记办成了这件事以后,在群众中提高了自己的威信,既解决了二哥的困难,又在全大队提高了二哥的地位,一举三得,可想而知我二哥应该感激到了何种程度。二哥为了报答王书记的厚恩,只能忘我地劳动,甚至抛弃自己家庭的利益积极地工作。他为了使全队人有饭吃,有钱用,真正是全身心地扑在改变生产队的落后面貌上。
在二哥接手当队长时,我们队上有一个贫困户,解放几十年了家里还住的是茅草房。这户并不是人懒惰,而是主要劳力常年有病,干不了活,更不用说改变居住条件了。二哥和几个帮手一商量,组织全队劳力去帮工,砌房庄,打土墙,帮工的人各自回家吃饭。
这是破天荒的事,那有一个帮忙干活不管饭的道理呢?二哥的做法虽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理解,但难免有一些人不满意,他们当面唱凉腔:“自古挣钱不挣钱,落个肚子圆。我们帮忙干活不挣他的钱也就罢了,怎么连饭都混不到吃的?”
这些人说的话都很在道理,也符合人之常情。二哥只好反复向他们解释:“贫困户正因为穷才需要大家的帮助。他家盖房之所以需要集体统一安排,主要是他没有能力管饭,如果有粮管饭也就不需要集体来撑头安排了。”
二哥对帮贫困户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一方面给做思想工作,一方面还要用实际行动去感化。那些离家比较远的,二哥干脆把他们留着叫在我们家吃饭。这是我二哥情愿安排的,本来是小事,也是好事,但他的义举却很快招来了众多群众的反对,大家一致指责在我们家吃饭的那几个人:你们给贫困户帮忙凭什么叫队长管饭呐?难道你们是给队长盖房吗?难道当干部就是这个落成吗?……
群众的呼声就是无形的力量,那几个人也感觉不合适,就不在我们家吃饭了,思想自然也“通”了。这几个人转变以后,全生产队对立的声音没有了,贫困户也很快搬进了新居。
二哥,就凭着公心,只忙着操心集体的事,忽视了对自己妻子的照顾。二嫂在生下儿子几个月就得了重病,他顾不上送医院诊治,一直拖着。当时我们那里医疗条件又差,可怜的二嫂在我侄儿出生不到一岁时就撒手人寰。
中年丧妻,这是人生的最大不幸。二哥在经受了如此重大的的打击之后,低落了一个多月。然而,生活是无情的,家里的衣食供养要靠他,嗷嗷待乳的儿子哭声促使着他站起来,生产队几百人眼巴巴地望着他,肩上的担子压得他不能自主,不许他继续沉沦下去。坚强的二哥在短时间的停滞以后,他把内心的悲伤变成奋进的动力,又迈开了跨越的步伐,带领全队人进入了改变贫穷面貌的战场!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但二哥的毅力却是感人的,耐力也是惊人的,他对家乡的贡献有目共睹!我难预料,老家的后辈将是怎样地评价那逝去的岁月。但我相信,二哥的功绩是永垂的,他的奋斗史将永远留于后代的口碑!他虽然干得不是惊天动地的伟业,但看看他的奋斗历程谁不为之感动:他刚刚踏入成年期当队长时,正是全队人在饥饿线上挣扎的关节。当时公社领导在谈到我们田山一队时都直摇头。他们用一个形象的比喻为我们一队的农民画像:“面靠火炉背靠墙,吃饭靠的是救济粮”;“面靠火炉背靠板,用钱靠的是救济款”。二哥当队长以后,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解决了群众的吃饭问题,两年家家有余粮,三年户户有存款。这些虽然从现在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事,但时代在快速前进,社会在不断发展。那个时候,对于年年“小麦黄,饿断肠”的贫困农民来说,有饭吃肯定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如果我们拿四十年以前的社会环境及其生活条件和现实相比较,那无疑会闹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笑话!
哥之所以能成为当时的佼佼者,他主要是办事能成事。他干事没有别的秘诀,全凭着自己的信念,那是全生产队老少都信服的一句话:要想为人民服务就得准备吃亏!这话接地气,容易懂,老百姓接受,也能从内心拥护他,跟他干。
当然,他是农民出身的低文化干部,既接受有政策方面的教育,也脱不掉因果报应的信仰。他常说:吃亏占便宜也有因果报应,当干部吃亏的报应就是群众真心信服,便宜占多了的报应就是群众一哄而起的反对;好事做多了自己心安,歪门邪道的事做多了自己心里迟早结个大疙瘩。长期胡作非为睡觉不安心,做事也不会畅快!
多吃亏既是他工作的信誉,也是他为人做事的准则!在几十年以后的今天,作为每一个立党为公的人都不可将这准则完全抛弃!
二哥之所以从年纪轻轻能带动几百人一呼百应,一干几十年成为“不倒翁”,正是由于政绩突出,当地群众拥护,上级组织信任。他在1980年又被选为大队长,带领群众修通了公路,架起了高压电,彻底改变了家乡的贫困面貌。后来他一直担任村民组长,年过五十多岁还放不下,几次要辞掉肩上的担子,一再要求让年轻人接替。但他的呼声和群众的信任声浪相比是那样的微弱,多次选举结果他都以压倒式得票连任。
二哥之所以能有好的口碑,是因为他自身具备有很好的德行。他当干部不是势利眼,他不巴结那些有钱有权有面子的人,而是专拣穷、傻和一些低能的人进行照顾。队上的五保户王苕真的是“苕”,他本名叫王秀德,小时家里很富有,念了十三年书才勉强能认清自己的名字,从那时起就众人就送给他了一个“苕”的名号(当地人把红薯叫苕,意思他像地里的苕一样死板)。“苕”的父亲是一个呆板的书生,望子成龙心切,被他这笨儿子气死了。王苕失去父亲就没有了依靠,在解放以后就成了五保户。现在他们老两口已经六十多岁了,老汉眼睛马虎,老婆仅能做饭。就是这样一家人,大家却开玩笑说比我二哥的岳父岳母都重要。那时队上收粮都是统一集中在一起堆成大堆,然后按照各家工分多少进行分配。这样当然在分粮以后和工分对不准,时多时少,缺了的下次补上,有剩余的时候二哥都是一口袋给王苕扛去。二哥的这种做法虽然是拿大家的东西做人情,但是众人看在眼里,喜在心里,只有一片声地叫好,并没有谁说半个“不”字。王苕面对二哥的照顾,倒还是有情有义,知恩必报。我记得最清的是有一年端阳节王苕给我们送礼,他给二哥拿了一盒山羊香烟(七分钱),一斤盐(一角七分钱),半斤红糖(一角八分钱),还有一碗爆花,这就是农村讲究的四水礼。母亲说王苕是可怜人,意思叫他拿回去。但是二哥担心伤了王苕的面子,含着眼泪收下了。并当着王苕的面,抓了几把爆花香甜地吃起来,过后留他吃了一顿饭。在王苕走时,二哥给他称了五斤盐,买了几盒火柴,舀了一升白米,二升苞谷。王苕推脱不要,二哥给提着送回去,算是回礼。
二哥“做人情”不止是对王苕这样的五保户,他公心面对的是所有的弱势群体。从现实说,生产队长已经是一个低到位的干部了,讲人权就是管了一些穷苦的农民,讲财权生产队一年就是那几个买化肥钱,这样的权限限制了二哥帮人的手脚。但我二哥聪明,会下棋,他把象棋上的原理运用于自己的工作中。他常说:不管啥事情总有解决的办法,就像下棋一样,车走不通了用马,马走不通了用炮。他本来是最反对“内亲干政”的,但在劳力安排上他却出奇地吸纳家庭人的意见。当时生产队每年要砍火地,——哦,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可能还不知道啥叫砍火地。砍火地就是把山上的粗细树木在树叶长全时全部砍倒晒干,然后放火烧过,就着柴灰开挖下种。这样做虽然破坏生态,但是土肥省力,粮食产量又高。这活路强度大,在山上整天被晒得口干舌燥,加上遍山荆棘刺手,妇女做不了。然而,生产队干活是统一的,妇女们不去劳动年终拿什么分粮啊?母亲见到这种情况,就经常要二哥照顾那些弱劳力。每逢母亲提这种意见,二哥总是言听计从。他把那些强壮劳力安排去砍火地,老弱辅助劳力叫去薅草,对那些有对象的姑娘们轮着叫到婆家去玩上几天。很多强壮劳力也知道二哥在玩弄“权术”,但谁家没有妻子儿女?谁能把劳力搭配得恰如其分?一季过后,火地砍出来了,其他闲活路也做出来了,群众没意见,年终粮食也是大丰收。
二哥对待别人仁慈,但对待家人却显得有些无情。当个人利益和集体的利益遇到冲突时,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抛开私情,捍卫集体利益,这在他唯一一次打我的一事中就是有力的证明。在我幼小的心灵,也正是从那次被打的事件中感受到了他那一身的正气。
那是他当队长的第二年,生产队修梯地,买了几个架子车拉石头。我们当时都很小,见了架子车觉得很稀奇,在大人们回家吃饭时我就推着架子车跑着玩。不想推到石坎边时我力气小扶不住车把,车子滚到了沟底。二哥到来时见架子车已经散架用不成了,他问清情况以后就抽了一个树条对我一顿好打。我虽然未成年,但是非界限能分清,我知道他不这样煞一下火气,再有别人弄坏了咋办呀?当时虽然感到痛,可我并不怪他,相反还有一点踏实的感觉。二哥在打过我之后,就自己出钱请来木匠,修好了架子车。别人上工,他又转过来对我作了细心的安慰。
二哥对我教育并不是一味地只用粗暴的方法,他对我更多的是关心和疼爱。即使是自己受苦受累,只要我能得到快乐他也感到舒心,我记忆最为深刻的就是他从山上背我回家那件事。
我上四年级的时候,我们很多同龄人经常上坡砍柴。有一个星期天,很多娃子一路上到离家七八里路远的麻梨沟垴去砍冬季烤火用的粗柴,我在往下放树时不小心手指被砸成两瓣,鲜血直涌,当时又疼加之惊吓,放声大哭。山下干活的人听见以后,赶紧喊我二哥。当时二哥正在挑大粪,那是十分繁重的活路,挑上几担就累得腰酸腿疼。但当他听到我受伤以后,立即跑着上山来了。冬天呐,我见二哥满头大汗,棉袄已经湿透了,背上冒着腾腾热气。我当时连感动带疼,哭得更厉害了。二哥没有多说,就在衣服角上扯下一片布给我作了简单的包扎,背上我就走。我见他太累,几次要下来自己走,他坚持不让。七八里路呀,他背上一个十一岁的兄弟一口气跑回家。这事我不但现在记得清清楚楚,而且终生都不会忘记!
在我上初中的第二年,二哥又娶了现在的二嫂,这一下给他的生活扭转了轨迹。但是,人口増多使我们原有的几件瓦房难以居住,二哥就借钱买了队上的公房另住。在分家时他没要一件家具,把全家在队上仅有的一百二十元余粮款全部留下来给我念书用。当时二哥买了两间房也才花了一百四十元钱,他给我留下的一百二十元钱可是一个家当啊!
二哥分家以后,逝去二嫂留下的儿子就由我母亲照管,他另居以后又连续添了两儿一女。这时,家务压得他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地步,再没有能力给我钱了。这之后,我念书的主要费用就由三哥挖药材和卖木料挣钱供应,间或父亲给人看病也挣些零钱作以填补。我两年的高中生涯,当时如果没有二哥留下的余粮款和三哥拼力的劳作,没有父亲的多方设法那是难以撑到毕业的。
世上什么伟大?父子之情伟大!弟兄之情伟大!我的几个哥哥,既是我的兄长,又是我的恩人,诚如古人所说的那样“长兄比父”,他们是人世间最好的人,也是我最为亲近的人!
我毕业以后,三哥被招入了社办企业。当时父亲已经年老,干不了重活,我自然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二哥虽然单锅另灶,但他不分彼此,见我不会干农活,就一直带着我,自动负起了照顾我们家庭的责任。
然而,二哥虽是处处好心,但他照顾我的第一件事却没有办成,搞得不欢而散,差点弄得弟兄之间反目。
当时农村初次实行生产责任制,打破了几十年来的大公统平生产方式,把生产队人员分成了几个组,全队的土地按照人力和劳力进行搭配耕作。我和二哥分在一个组,内有几个调皮的人不和邦,他们今天说干部不出力还要拿工分,明天说别人干活不出力,伙同起来上坡闹罢工。二哥看到这种情况很着急,他知道这样一直闹下去肯定要散伙,弄得大家没饭吃。他是大队长,经常从报纸上看到其他省的很多地方已经包产到户。于是他召集大家在一起分析,认为我们这里当前的包产到组只是包产到户的前奏,下一步绝对要按照外地的方法包到户。迟分不如早分,分到户既能调动大家做活的积极性,又能使生产管理省去了很多麻烦。于是,他组织几个人把我们组上的土地评出产量,按照人口产量占60%的比例,劳力占40%划到各户。
土地开始下划时大家异口同意,但是在公布定局方案时却爆发了激烈的矛盾冲头!本来,包产到户就没有上级文件支持,属于偷偷摸摸的行为。但是占地的农户却不管这些,他们都争着占好地,都不要差地和远地。这倒难住了二哥,他是干部,弄出这种不可收拾的局面咋办呢?
没办法,二哥只有老办法——自己吃亏!当时我不会做农活,二哥自然把我们的土地搭配在他一起。开始的时候我们好地就分的少,但我看到二哥工作为难,加上他干活是一把好手,另外又有他对我的疼爱之情,我不可能跟上别人给他出难题。这样,尽管他怎样决定我都服从。可是现在不同了,那些吵闹的人缠得他无法,他就想了一个息事宁人的办法,把我们名下的好地和别人兑换成了瞎地、远地。这无奈之举虽然平息了矛盾,但明显的是我们辛苦劳作一年要做一大半的冤枉工,年终连自己的衣食都顾不住。
岂有此理!都是凭土地吃饭,我为什么要把好地让给别人?
我开始和二哥论理,意见不统一就和他吵了起来:你不要好地我要,你不吃饭我要吃饭,我凭什么要绑到你这棵树上吊死?
我和二哥吵起来以后,惹动了那些想当干部而又喜欢看热闹的人赶来围观。他们认为二哥长期当干部没有给他们让位子,本来就有意见,这一下倒有了向上级反映的口实:看,看,大队长在胡整呢,连他的亲兄弟都反对!
实践证明,一个小小的农村干部,如果想干那些没有上级支持的事如同上青天!二哥的包产到户行为很快被上级当作反面教材进行处理,公社派来了一位姓邹的武装部长,带领了一个工作组进驻到我们生产队进行处理。
邹部长带的工作组一个个杀气腾腾,他们撇开二哥这个大队长不见,背地里召集大小队的干部会议,要求大家对二哥私自把集体土地下划到私人的做法谈认识,定性质。那天会议讨论得非常激烈,每个人对这种行为作了愤怒的声讨。其中三队队长老李特别积极,他性情激昂地说:“当前这种包产到组的政策就已经好到顶了,我是双手赞成。现在大队长还要包到户,这明显是要回到解放前的私有制嘛!我建议把土地重新收回,对责任人逮捕法办!”
邹部长到底是公社干部,站得角度不同,所以看问题有点接近于高瞻远瞩。他知道老李窥探大队长的位子已经很久了,一心想把我二哥整倒自己顶替,这已经是大家十分清楚的事。老李说的处理办法一方面明显过激,另一方面要逮捕人,自己一个公社干部又没有那么大的权力。再说,大队长搞包产到户是参照外地的经验,尽管咋说也够不上刑事处分。思之再三,这位圆滑的部长最后决定要我二哥自己纠正包产到户的做法,收回土地,并在全大队群众会上作检讨以挽回影响。
二哥初开始并不接受工作组的处分,他的理由很强硬:包产到户只是按照报纸上介绍的经验办事,我们只是照做而已!
但是,邹部长说话就如同领公社领导一样,是“圣旨”,一个大队长怎能犟得过?世上只有桶掉到井里,哪有井掉到桶里的事?扭来扭去搞了三天,二哥到底低了头,向群众公开作了检讨。
二哥从十八岁当队长直至大队长几十年,每年都是上级表扬奖励的对象,他在什么时候受过如此大的委屈?总结他当干部的经历,就和一颗没有经过风吹雨打的树苗好有一比。哪些长在荒山野岭的树常年经受风吹雨洒,就是再有多么严寒,哪怕电闪雷鸣也能经受得住。而温室的苗木从未经受恶劣环境的袭击,稍遇风雨严寒就会夭折。当干部经常挨批评就像风雨里的大树,窝一次,折两次对他们来说都不在乎,因为习惯了!但从来没有经受过批评的干部就像那没经过风雨的弱苗,遇到一次批评处分马上就受不住了。我二哥的干部生涯就如同那颗弱苗,这次邹部长给他上的王法犹如迎面给了几巴掌,他当然受不了!他的积极性被打击殆尽,他不干了!
二哥搁挑子不到半年,上级来了政策要求全面推进土地包干到户工作。这次好了,从大气候方面证明了二哥以前的作为顺应社会潮流发展,他做事具有别人无法比拟的前瞻性。哈哈,那些以前反对他的人现在就像缩头乌龟,就连见人也是低着头。他们根本谈不上再敢批评二哥,更不用说叫他们搞那些以前认为违背政策的包干到户工作了!
公社清楚我们队上是一个烂摊子,就叫我当大队会计。领导们给我肩上压住胆子以后,就由公社书记去给二哥做工作,要他重新负责大队工作。
二哥开始任从怎样说都不干,最后公社书记只好打出“人情牌”,用一句话把它塞死:“你兄弟才开始当干部不熟悉,工作上指望你传帮带呢,你这样做不是拆他的台吗?”
嗯,这话管用!二哥没法再推了,只好乖乖地按照书记的话上了岗,以师傅和兄长的身份和我联手工作。
我和二哥共事不到两年,适逢公社信用社招合同工。这下我的三哥也是福星展开了手脚:三哥在社办企业开着全公社唯一的一台大型拖拉机,这是全公社最的独门,就连领导们也经常求他办事。三哥虽然文化不高,但是相当聪明,属于高智商的人。他不但对于机械方面的知识有着天生的悟性,而且在社交处事方面上下左右照顾的很全面,在我的大脑里他是一个天才的社会活动家。三哥这方面的优势自然成了我仕途上的强大后盾,当他得知信用社招工的信息时自然动用了全方面的关系。他的主动反倒把我比成了闲人,因为我一个大队会计只有一个小小的活动圈子,和他的人气相比简直不在一个档次,一切托人找关系的事都是他帮我代办。信用社的朱主任是三哥的好哥们,加之二哥当了多年干部和他很熟悉,另外主任也了解我在大队的工作很出色,于是就尽力地为我上下打点,把我招进信用社工作。从此我就跳出了“农门”,别过二哥端上了公家的饭碗。
在信用社工作不到两年,适逢一九八四年基层组织改革,搞政社分设,把公社改成乡,大队改成村,小队改成组,我就在那次改革中被选成了副乡长。我二哥却在那次机构改革中辞去了村干部职务,最后我们组上的群众不同意,把他选成组长,一直干到五十多岁。
都说二哥放下村干部的担子,这一下有了精力摆弄自己那几亩农田,好日子在向他招手。但是,有谁能想到神鬼无眼,老天无情,将灾难一个接一个地降到他的头上。这些事虽然过去了很多年,但我至今回想起来仍然觉得毛骨悚然。
二哥受的第一次灾难是在一九八九年秋。那天他帮人打核桃,不意雨过初晴,树上光滑,从五米高的树上滑落下来,跌成重伤。那时,他的大儿子茂琦已上女方门去招亲,家里还有二儿子茂雪、三儿子朝义和小女爱玲俱已到成年,几个儿女都非常孝顺。二哥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在孩子们的精心照料下,身体慢慢地恢复了。
我原以为,按照古人所说的人有大跌必有大闪,二哥已经受过了劫难,下一步肯定是要闪起来的。谁知,那些轮回报应在二哥身上全无体现。他在受伤后的第九年冬又从车上摔下来,伤势比前几年那次重得多,整睡了三个月。可怜啊!
苦命的二哥,他以前受的伤势我们能想办法使其恢复,但在后来精神方面的一次次创伤就是神仙也难医治——
2003年夏季,二哥的第二个儿子茂雪在山西煤矿出了矿难,这一下他就被打击的摇摇晃晃。那知,冥冥之中掌管人间福祸的黑手还是一直惦记他不放,在2008年夏季,他的小儿朝义开车给工地拉沙时又出了车祸,留下了一个仅两岁的儿子……
接连的无情重创,二哥就是铁人也经受不住了。以前受伤的身体每况愈下,加之精神接连受到打击,他只有借酒浇愁。谁知,“一醉解千愁,酒不解真愁”!他清醒时感觉愁,沾酒感觉愁减轻,酒醉稍能安慰一下心灵。这样,人生无奈的二哥染上了酒瘾。
他的身体本来就很虚弱,朝也喝酒晚也醉,进入了恶性循环的状态。他已经万念俱灰,只想早早地告别人世。是啊,人就怕绝望啊!
但是,当看到大儿子茂琦那聪明的一对儿女,当望着朝义留下的那可怜儿子,当想着小女爱玲在远方带着一儿一女,他的心陶醉了——五个孙子啊!这些可爱的儿女和孙辈们带给了它新的欢乐,他心里又有了生活的希望。
二嫂见丈夫心情逐渐好转,强压住内心的悲痛,尽心地照管二哥。她竭尽全力挑起家务的重担,学会犁地、播种,在做农活和做家务重活时只是把二哥当成一个助手。二哥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二嫂当帮手。他逐渐地恢复着,盼家庭日子好转,更盼儿孙们平安幸福。
是的,有二嫂这个好伴侣,有可爱的儿孙们在膝下,二哥应该感到欢欣,应该感到安慰!
但是,孙子们不可能整天陪伴着爷爷,当他们到校去读书的时候,二哥遂又感到心里无限的空虚,无尽的烦恼,无边的悲凉!
人烦恼,人悲伤,烦恼悲伤都有两行泪。而我的二哥,他是大丈夫,伟男子,他在烦恼悲伤的时候只能强忍着泪水,有的只是长长的叹息……
二哥想不通:自己几十年帮别人安家立业,为何自己家道不顺?自己一生助人为乐,为何自己落得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几十年奉行的是“把别人孩子拉一把,自己孩子长一搾(一拃,一般是拇指和食指伸出的五寸距离,在这里比喻长高度)”,为何天灾人祸不断降到自己头上?苍天,苍天,苍天啊,你为何如此不公?
这些,二哥想不通,我更想不通。
我二哥一生怀着对人间的大爱奋斗不止,他关心弱势群体,为家乡父老乡亲的冷暖牺牲了个人的前途,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山区人民的事业,最后默默地带着一腔悲愤离开了人世。我不止是想不通二哥想不通的问题,更有面对的现实増添新愁:世上别人在生日期间都遇的是喜事,而我的生日却是二哥的告别人世的日子。别人生日有谈不完的快乐之事,露不尽的欢声笑语,而我的生日却要把二哥生前经历的“流水账”在大脑里细细地回放。这样的日子里,我怎能高兴的起来?
我回忆一遍问一遍:这愁结,何日得开,何时是尽呐?
(二零一七年农历九月十八日)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
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刘萧姣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