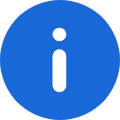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一)
我在冷水乡的一届乡长任期已经满了,县上经过考查,调我到阳山乡任党委书记。
我的工作调动之后,冷水乡的班子也作了一次大变动:孙成退居二线当了主任科员,结束了多年在冷水乡叱咤风云的历史。他的人大主席的职务由继续留任的乡党委书记袁新兼任,原来的两个副乡长继续留任,职位没有变动,向明杰接替了我的乡长职务,他的副书记职务由公路专干李晓新担任。从此,我就再也无缘继续搞老家的乡村工作了。
我一想起阳山乡就觉得好笑:这个在我读书时假期经常掮椽子路过的地方,沿路很多人家是我经常讨要水喝的。那时,他们有的人见到我们这些下苦力掮椽子卖的人时,总是有一种看不起的神色。记得有一次我们掮椽子遇到了下大暴雨,把椽子靠在一个姓钟的人家门上,想进屋去躲避一会儿。谁知,他见到我们来时竟“咣”地把门关上了,我们只好在他家的房檐下立了半天,一直等到雨住了才走……现在,我就要在这个地方来管他们了,你说这事滑稽不滑稽?
我到阳山乡后,单位照例先是一番酒席接待。宴会结束后,人大主席张才升来找我座谈,并详细地介绍了情况:
“我们乡上的农业人口是八千六百多人。现在从整体来看,农民还是听话的,因为前几年叫乡上搞计划生育整怕了……”
“计划生育又不是人人过关,咋能说都整怕了?”我有些疑问。
“嘿呀,田书记,你不知道,”张才升说着脑袋直摆,“我们乡上自古以来山高人稀,旧社会就是那些杀人土匪躲身的地方。一代代沿袭下来,就形成了大姓宗族少,多数地方一个院子几个姓。也正是由于这样杂姓多的村情结构,才养成了人情世故比较淡薄的民风,相互之间谁对谁做事也没有什么感情。很多人不听干部们的话,上级政策他们又不愿意执行,大部分育龄青年对计划生育政策认识模糊,很多妇女有超生,乡上干部直接没办法。”
“我原来听说你们这里计划生育搞得好嘛,咋整的?”
“唉,在撤区并乡的前一年夏季,区上集中了六个乡的干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把全乡超生的对象罚了二百四十多万块钱。那时,全乡每个受罚的户把自己存的钱和能贷到款的钱全部交了都不够,他们只有向亲戚借或者托朋友贷款,这样就使那些没受罚的户也跟着出钱。你看么,我们这样一个农业乡,以前也没有个啥主导产业,经过那次一整,农民这多年都爬不起来了。当时的区上书记姓柴,这清收的主意是他出的,到现在大家还在说:‘区委书记柴‘拐子’,把农民整得打摆子’……”
“看来农民这一块发展什么产业的困难是大一些,现在乡上干部的精神状态如何呢?”
“乡上自从那年在修小环路时把整班子的领导干部撤职以后,一般干部一直没有调动过。现在的领导班子情况也有些复杂,几个副职干部都在观望,新来的乡长冯自章,人倒也还诚实,就是一天到晚只知道喝酒,喝醉了就在乡上的院子里混吵一气,有些人喊他‘疯子章’,还有的人说他是‘章疯子’。唉,你来了,工作还是难啊……”
果然,张才升没有说错,冯自章真的是一个不怎么称职的乡长。我到单位召开第一次乡上领导干部会时,提出应该先开个村党支部书记会,让大家汇报一下各自村上的选举工作情况。按说选举是依法运作的大事,乡上的书记新到,理所应当要召集村干部们汇报一下情况,以便一把手能掌握各村的动向。另外也能使新来的领导和大家互相见面熟悉一下,这是稍有常识的乡长就应该主动提出的礼节性工作会议。谁知,当我提出意见之后,冯自章却极力反对,他十分不高兴地说:
“最近的工作都安排好了,大家心里都是清楚的,开会有什么意义?”
这家伙,连一点同事之间的情面都不顾!我不好直说,一再解释说选举是大事,我跑了几个村发觉还是存在有一些问题,乡党委应该及时掌握全局动向,加之选举代表又不同于其他工作,一旦出了差错是无法弥补的。他不但不听我的安排,反而还振振有词地硬顶起来:
“选举还有什么问题?哪一个村上敢出乱子?谁摆下了乱子谁负责,这些我们都掌握好了!”
这一下我真的来了气,就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组织安排选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我这个一把手至今连选举的动向都不清楚,如果只听别人说,到时候出乱子了难道还能把别人推出去向县委交代?再说,作为礼节来讲,我来单位这么多天了,也应该在正式场合和大家见个面!”
这实实的一棒子,“揍”得冯自章不言语了,就只好安排起开会的事来。我会后看着他那忙碌的样子,不由地暗自感叹:这伙计,为什么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呢?
通过这件事后,张才升向我介绍说:冯自章对我到阳山乡当书记不满是有各方面根源的,主要是他在乡镇领导级的岗位上跳得太快,可以说,领导岗位上他还处于涉世未深的幼龄期,甚至连组织上用人的程序都不清楚。他原来是河边乡的一个蚕桑技术员,在撤区并乡时抓了一百亩的桑园密植点,当时恰值全县大力推广种植密植桑之际,这可谓适逢其时,组织上就提拔他在本乡当了副乡长,乡上仍然叫他分管林业。这冯自章搞具体工作时真的有一股子牛劲,他在当上副乡长之后抓林特园示范点时,整天和群众一同挖窝子,修剪树枝,对乡上的领导工作很少参与。他这样搞,从名义上来说是一个副乡长,而实际干的是林业技术员的工作。当阳山乡在修路过程中出现了伤亡事故时,乡上的干部对于这事没有安排好,加上内部又搞窝里斗,因而几个主要领导都被免了职,这时恰值全县的乡镇班子刚安排定序。县上在调整干部时,考虑到冯自章所在的乡镇领导职数比较多,就把他提拔到了阳山乡当乡长。有着这些前因,他就在酒醉时经常向别人炫耀:“人要有真本事。你们看我都四十多岁的人了,三年时间还弄了个正科级!”
原来如此!熟悉乡镇工作的人都知道,一个正科级干部在高级单位里,可能只是做一些具体写写算算工作的办事员,有的甚至是什么责任也没有负,只是为了享受待遇而定的级别。就是县上各单位的主任科员,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自由的,一天到不到单位也没有人过于追究,一月工资与在岗时一样对待,你不服气也没办法,他们都是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的,以前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他们是按照上级安排退居二线的,现在相对工作量小一些,单位领导也不好给他们分配什么具体事务,因为县上安排人事时是科级干部到了五十岁都要退,一刀切,哪一个说不愿退,还有精力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做贡献,难道别人就不能做贡献?你有的能力,大家谁没有?县级单位就那么几个位子,换一茬领导虽然说不上是一朝天子一朝臣,但是重点的几个对象总应该提拔一下吧?都占住位子不退,这些重点对象朝哪里摆?再说,老龄干部不退下去,难道能叫年轻干部在办事员的位子上待一辈子?从这个角度来看,哪一方面都有包袱,这包袱就看谁背!话说回来,人事安排到乡镇就不同了。一个乡镇的科级干部,除开上级调入的人提拔起来比较快一点以外,你如果从头做起,在单位里硬磨,不干出一些特殊的功绩,就是熬到县上的科级干部退居二线的年龄都当不上科级干部!再说,真正要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乡镇领导,不是说会搞科学种田,配方施肥,林业管理这些知识就能成的。当然,这些知识固然是乡镇领导应该具备的,但它不是唯一决定的条件。一个合格的乡镇领导在工作中应该是上懂中央政策,下知鸡毛蒜皮;既要与上级组织保持一致,也就是常说的猜测上级的工作意图,又要结合本地的农时季节,该栽树时栽树,该种地时种地,一个时期有一项工作重点,不能搞成串脸胡子吃糨糊——一模糊。在生活中要上能上国宴,下能下贫民窟。在特别困难的时期遇到上级来检查,作为乡镇领导就不应该一味地叫苦叫累,还得把哭脸藏起,拿出笑脸来给上级领导看,以取得上级的理解、信任和支持,绝对不能把困难向上级一推了事。不然,上级把你安排在这里做何用处?总的来说,乡镇领导在百姓眼里是父母官,要管着几千人,有的甚至管着几万人的吃喝拉撒。像这样的角色,岂是三两年就可以成就的?
诚然,冯自章在上乡长时是有些急促。这些,在组织部钱副部长给我谈话时就已经提及过。钱副部长与我们很熟悉,和我谈话结束以后在议论班子人员时,他把话语说得很婉转,也很巧妙,但是意思我还是听明白了:在阳山乡处理一套班子的领导时,正值全县一次提拔了二百多名科级干部不长的时间,也是库存后备干部用的竭乏之际。仓促之间,只好凭印象用了几个稍有影响的人去顶缺,无暇顾及完全成熟与不成熟的问题,更不可能去做多方面的考察和求全。这正是应了古人所说的一句话:“蜀中无大将,瘳化充先锋。”
组织上的考虑,冯自章根本不知道。他在阳山乡当了两年多乡长,换届时知道乡上的书记要调走了,满以为自己顶替书记职位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这时县委组织部早已经过长时期的选拔考查,对全县各乡镇干部的状况全部掌握清了。他们认为冯自章虽然年龄有四十多岁,但在掌握全盘工作方面还属于“不成熟型”,不宜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就安排他任了原职。
冯自章可不管组织考察不考察的事,他总认为自己没有当上书记,是新来的人挤了他,因而就对我采取排挤的态度。他有几次喝酒醉了之后,就在乡政府的大院里寻事辱骂几个干部:“都不球好好搞工作,工资发不下去又没人管!到税务所去要税款都不说咋办,我给送礼了别人还说要注意工作方式,都当的是啥Q领导?我把公路修通了,高压电架好了,机关单位电灯也亮了,马上就来人领导我了?”
这冯自章说话的意思很明显是针对我而来的。若在前几年,我非顶得他翻白眼不可!但是我现在得忍着,因为我能成为一个乡党委书记,是经过组织培养了多少年,自己也是做了长时间艰辛努力的。现在站到这样的角度,是管人的,是要做人的思想工作!作为一把手,容人之长容易,容人之短却难,正因为难,才要求一把手去做!我不可能叫别人经常来提醒我,也不可能经常问别人我该怎么办,我的一切一切都要自己管理自己,自己约束自己,我怎么能和一个醉酒的乡长在大院子里吵闹呢?要是那样的话,单位又有谁来拦挡我们,同志们会把我看成是什么素质的领导啊?还是同志关系要紧!再说,冯自章也不是坏的不可救药,他也有可爱之处。平常不喝酒时,对我还是客客气气的,他也知道自己考虑问题欠周全,说话总是带着请教的语气,我每次安排什么工作他都尽力去做。这就够了,要顾全大局!
由于我经常这样地提醒自己,对于冯自章处处忍让着,单位倒也相安无事。那天,我们乡党委开会,研究了两件事:一件是到县上计划局去联系,要一个项目,把乡政府门前的两公里河堤加固一下;另一件事是召集村主任会议,安排近期各村工作交换检查的具体事项。这两件事本来都是应该由冯自章牵头办理的,但是他却提出自己和县计划局的人不熟悉,请我去联系,他在单位负责开会。我一想,这是实际情况,乡上以前与计划局联系的也少,现在我出头去找计划局联系,事情自然比他们去要顺当一些。
散会后,我们兵分两路,干起了各自的工作。我在计划局办完事后,刚出门就遇到了县委办的秘书小王。这小王往日见了我总是要先说笑一阵的,今天见面时他那神情好似很诧异:
“你咋还在这里呢?”
“咋了?”我也感到很惊奇。
“你们乡上的东沟山上失火了,市政府办公室和市林业局的人上午就到了县上。刘县长亲自率领县上的十几个单位到山上扑火去了,刚才你们乡上电话报来的情况说火势大的很,估计已经烧了六百多亩了!县上已经通知邻近的五个乡镇,要求每个乡组织一百名以上的人员到你们那里去扑火呢!”
“天啊!”我顾不上和小王闲谈,就急忙搭乘了一辆出租车,向乡上赶去。
出租车在飞跑着,我的思绪也像车轮一样飞速地转着。车子沿着汉江河直下,那缓缓的河流逆着出租车连同对面的山脊飞速地向上游穿去。我顾不得欣赏这些美景,只是一味地思索着:现在摆下了如此大的烂摊子,这个场子该怎样去收拾呢?
……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二十九章:【怎样评说】(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刘萧娇
责任编辑:肖海娟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