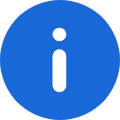离家数十载,尝遍五湖四海的佳肴—皮黄肉嫩的广东白切鸡,红浪翻滚的四川麻辣火锅,生猛鲜活的海鲜大餐,热气腾腾的关东一锅炖,可萦绕在舌尖的,永远是家乡的柴火饭菜,每每想起,心中总是充满温暖与幸福。
记忆在平静的时光中潺潺流动。深秋的一个傍晚,母亲望着天空翻腾的云层,嘴里念叨着:“今夜要是刮大风,明早我就四点起床扒柴,不然去晚了就没有了!”果然,呼呼的风刮了一晚。恍惚间我听见母亲窸窸窣窣地穿衣声,她在杂物间穿梭,不一阵便听见“哐当”一声的关门声,她出门了,天还没亮。天渐渐破晓,我起床睁着朦胧的双眼站在门口张望,只见母亲一身柴屑,蓬头垢面,佝偻着背,背上背着满满一篓干树叶,手里还拖着两根树枝,把这些放在地坪上便对我喊:“琼伢子,把哥哥姐姐喊起来,今天山上好多柴,我刚刚已经扒了几堆在那里,我们赶紧去,免得被别人收走了!”
那个年代,柴火是农村人的命根子。只要到了干燥多风的秋冬季节,家家户户都瞅着天,期盼着风大一点,吹落的杉树和松针树叶子可是几好的点火柴。而枝干,则是每家必备之过冬大柴。平日里刮风吹不动枝干,只有等父亲从单位回来,与母亲、哥哥,戴上手套,带着柴刀、木梯子,在一个天刚蒙蒙亮的清晨,到自家山上,把那梯子架在参天大树的树干上,仰着头,掂起脚,咬着牙,使尽全身力气把枝干砍下来。枝干尖锐,父亲经常是面部或脚部被划伤,他也不管,任凭鲜血淋漓,继续劳作。母亲带了篓子,把父亲砍下来的不便捆扎的树叶用柴耙全部扫进篓,哥哥则把枝干砍成方便捆扎的形状等父亲来捆。父亲扯根不知名的藤蔓,三下五除二便把柴捆得扎扎实实。说来也是奇怪,看着很大一堆柴,散落在各处,在父亲的几下摆弄之下变得齐齐整整,服服帖帖,看得人心生佩服。

砍回来的湿柴是需要晒干才能烧的,父亲经常是没日没夜的砍,几天时间,屋前的地坪上便堆满了柴。如果是树干,干了后还要劈开,这又是一个力气活。父亲先是用锯子把它锯成一段一段的,再用斧头挨个劈开,然后与母亲一起把劈好的柴码在杂物的墙边,码得整整齐齐,直到那一面墙都满满当当,瞅着心里才踏实。至于手上因劈柴磨破的伤口,压根就不值一提了。树干耐烧,通常只有过冬才舍得烧,寒冬腊月,推开门走进来的那一刻,望见炉灶那一团跳动的火焰舔舐着黑铁锅,冰冷的脚趾便暖得发烫了。
用柴火慢煨的锅巴饭是很香的。母亲把米淘进被炉灰烧得焦黑的尖底砂锅,待饭煮到八成熟,便只留一根柴燃着微小的火苗,慢慢煨着,直到砂锅里散发出淡淡的的饭香味,便把火熄灭,把锅垛在散着余热的火炽上。待菜熟了便揭开锅,一阵浓浓的焦香飘满厨房的每一个角落。锅底的锅巴是黄色的,粘连在一起,一铲子下去,发出清脆的声音,咬一口,嘴里“咔嚓咔嚓”作响,那味道里含着杉树、泡桐树、松柏树的清香,真是一口一个满足。倘若是放上两个红薯一起煮的,红薯的甜糯就会让这香味更加醇厚。
父亲厨艺好,但鲜少在自己家下厨房,但是,杀年猪的时候除外。母亲年年喂猪,但猪不是年年都能舍得自家杀,家里四个孩子,能卖一点钱就还能给孩子们攒上来年的学费,一人买一件新衣裳。所以,如果听说过几天会杀年猪,我们几个就盼星星盼月亮,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到了那天,那个杀猪的远房亲戚早早的就来了,父亲还叫上叔叔婶婶们、叔爷爷叔奶奶、老石等过来帮忙与吃杀猪菜。母亲笑吟吟地抱出一把大柴,生出冲天的火焰,众人热热闹闹坐在火堆旁,嗑着瓜子聊着天,等师傅杀猪再帮忙做事。
男人们按的按猪腿,按的按猪头,不多时,随着一声尖叫,众人欢天喜地,处理猪血的、吹气的、淋开水的、刮毛的,一切都井然有序地进行着。父亲则把师傅递过来的热气腾腾的猪心、猪肺、猪肝、肥瘦相间的前腿肉、猪血,足足有五六斤,简单处理一下,招呼母亲把灶间的火烧旺一些,在大锅中放一大勺猪油,烧得油冒烟,下入姜蒜,紧接着就把杀猪菜下入锅中翻炒几下,倒入开水,盖上锅盖,任由锅中翻滚。那浓郁的香气肆意弥漫,足足飘出半里地,连外村的猫猫狗狗都被引过来,在坡上盯着我家,口里流着哈喇子,却又怯怯不敢上前。根本不需要别的配料,只需要把火烧得旺旺的就行,起锅时放两根母亲种的大蒜苗,便大功告成。一大盆杀猪菜,加上昨日父亲提前在塘里网的大草鱼,再炒几个下酒菜,众人便围坐桌前,享用美味。我也顾不上烫,嗦溜一口杀猪菜汤,再夹一块肉片塞进嘴里,鲜、香,甚至还有一点清甜,简直就是最幸福的人间烟火味。父亲那天心情特别好,他借着酒劲,扯着嗓子说:“今天这猪儿杀得顺畅,没有跑,那我们家来年也能顺畅地过好日子了!来,为了我们大家的好日子,干一个!”我没懂意思,后来才听大人们说,在我们老家,杀猪的时候猪儿跑了是不吉利的象征,却不知有无依据,世间万事,谁说得清楚呢!
时光匆匆流逝,父亲已逝去十余年,他健在时砍下的满满一杂屋一墙垛的柴直到去年才烧完。母亲年事已高,已很少烧柴,而是改烧液化气。不过知道我喜欢吃柴火饭,母亲便经常会到堆满柴的山间去搂些细枝干叶回来,给我烧几顿香喷喷的饭菜。走在山间,母亲感叹:“原来的柴火要靠抢,现在这漫山遍野的柴火干得腐烂了都没人要,要是你父亲看到了准会一根不落的捆回家,把家里杂屋的角落都堆得满满当当!”我扶着蹒跚而步的母亲,透过林间参天大树眺望天空,似乎感觉到父亲在遥远的地方看着我们,守护着这一片山林。
本期编辑:萧筱玥
责任编辑:陈羽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