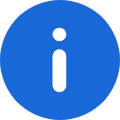我叔父任登庚的长篇小说《变迁》,集史料和艺术为一体,读后使人感触颇深。我经过反复阅读,感到最欣赏的还是人物丰富的语言,其中尤为深刻的是:保长王水成请客;田自新请田自智帮忙调整土地;田自智动员田自贵和何爱花两口子去做计划生育那几段对话,简直到了绝妙的地步。
下面,就小说描写的几个过程作以欣赏。
先看王水成请客:
“王水成在参加竣工仪式之后,对九保的人把好话说完,总算接到了家,陪同李坤山。他把贵客接到后,真是应了古人那句话:老鼠添猫鼻子——不要命的巴结。他在保上专门安排了八个人陪着,叫人在门外场院搭起八卦篷,摆起了四个八仙桌。白天的招待倾其家中所有,无非是些鸡鸭鱼肉;夜里赌博,灯火通明,尽兴方罢。如此大筵三天,李坤山整天有李秘书玩过的情人陪着,在迷迷糊糊当中竟‘赢’了五百多块大洋,九保的两个保长都‘赢’了二百块以上。”
这一段,作者用了简短的一句歇后语:老鼠添猫鼻子——不要命的巴结。一下子就把王水成那种奴才嘴脸勾画的淋漓尽致。
再看主人公和田自久吵闹之后被堂兄将军的那一段。小说是以第一人称写的,田自智(小说中的“我”)是大队会计,在土地大包干的工作中,具体负责着本生产队的土地调整工作,可谓大权独揽。田自久是户口在本队而人又在外地教书的民办教师,他的胞兄田自新原来分的差地多,现在属于要多得一些好地的户。按照当时公社的规定,田自久这种情况在教书的队上分地,不能在本队分。当田自智把分地的方案公布以后,田自久不服,并和他吵闹。年轻气盛的田自智占住了理,就是不报复他,不给分地也属正事正办。
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人是没有办法转这个弯子的,似乎田自久得不到土地已经成了定局之事。但是,田自新硬是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田自智,使他改变了观点,给当天骂自己的田自久帮起了忙:
“我一个人正在思谋着社员会怎样开的时候,田自久和他哥哥田自新一起来找我反映问题。
田自久气呼呼地说,他是看了我们在外面贴的分地方案以后才来找我的,并问为什么把他家里少算了一个人?我给他解释说公社有文件规定:民办教师的土地应该在教书的队上给划,户口所在地不管。田自久死磨硬缠地叫我给他再增加一个人,我当然是据理不让,这样说着话不投机,就吵了起来。
我们田家坪院子的很多人爱趁热闹,在田自久和我争吵的时候,不一会儿就围了一大圈人。他们有的是出于对我工作的关心,来到这里劝架的;也有的纯属于消遣赶热闹,为了瞅着院子这两个有文化的人吵架好玩;还有的是准备给我帮忙,如铁锤子和田自稳几个年轻人。
田自久见一下子来了这么多的人围观,也就越发地来了劲,越吵越凶,并且还骂了起来。这下惹恼了铁锤子,他刚知道我给他家解决了土地的问题,这时见田自久和我吵闹,怎能袖手旁观?当时就扑上去一把抓住田自久的衣领,照着脸就给了一巴掌。他一边打还嘴里的唾沫星子乱飞,不住声地骂道:
‘你田自久是个不成器的东西,像个啥子教书的?嘴巴放干净一点,跑到自智哥门上来吵啥?’
铁锤子这一巴掌打得狠,田自久当时左脚腾空,右脚着地成为轴心,脖子向右一拧,在原地打了一个圈。待他再次面向铁锤子时,脸上明显有了几个红指印。
田自稳也立在旁边,握紧拳头助阵:‘好好打这瞎东西,他若不是皮痒了才怪呢!’
田自久回身抓住铁锤子,恼怒地骂道:‘杂种铁锤子,我说的事情与你有个球的相干,你来打我干啥?’
‘来,我教你知道干啥!’铁锤子说着又是一巴掌。这一下,田自久耳内鸣响,眼泛金星,嘴唇发乌。他捂着脸摇了摇头,双手胡乱抓,把铁锤子脸上抓出了几个红痕,声嘶力竭地喊着:‘我和你拼了!’
‘你狗日的来拼一下试试!’铁锤子这时攥紧拳头,照着田自久胸脯直捅一拳。这一下,田自久如何能当得起?当时摇晃不稳,后退了步,一屁股蹲了个仰八叉。
田自稳在旁边手痒痒不过,要扑上去给铁锤子帮忙打田自久。田自新见不对头,急忙挡住。他又转过来张开双臂护住田自久,嘴里气呼呼地嚷道:‘自久,你不想吃饭了?还要土地不?’
铁锤子直把田自新往开推,骂道:‘你狗日的田自久敢再张狂,今天我就送你回老家!’
田自新急忙又把铁锤子拉住,‘哎,兄弟,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不要打了!’
田自久见他哥不准和铁锤子打架,也就跛子拜年----顺势一歪,感到正好给他弄了一个台阶下。他知道铁锤子力气大,拳头出来也像铁锤一样。现在仅仅只给了他一下就感觉胸腔闷疼,再这样缠下去今天非成残废不可!他清楚我不会打他,当下就揉了揉红肿的脸,向我扑来直嚷嚷:‘公社那是个啥Q规定?照那样说,我如果不在现在的学校教书了咋办?’
我也毫不客气地回答:‘那你去问公社,不是我管的事!’
他在铁锤子那里挨打受了气,想在我跟前挽回一点面子,当下就拍起了桌子,‘我今天就是要叫你管!’
我也很气愤,把桌子拍得比他还响,‘田自久,这是政策规定,又不是我搞的,你还当我怕你不成?你再在队上胡骚情,我给辛主任说,叫你连书都教不成!’
那边,铁锤子见田自久在我面前发威,就挥舞着拳头直扑过来,‘自智哥,打他狗日的!’
田自久见铁锤子向他扑来,知道还手明显是吃亏。他机灵一动,当下摆出了大将风度,双手抱胸,以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姿势立在那里,口里发着硬话:‘铁锤子,我今天不动手,看你敢把我打死才算真英雄好汉!’
铁锤子见田自久摆出了这种阵势,当下也就立住脚,用指头直捣着田自久的额头,恶狠狠地骂道:‘你狗日的嘴硬嘛,你再硬一下我看!’
‘算了,算了,都回去!’田自久的救星田自弟刚好赶来,拉开了铁锤子。
田自新看到我有几个人在场帮忙,再吵下去田自久还要挨打。他见田自弟拉开了铁锤子,就赶紧示意几个看热闹的人帮忙,死拉活扯地硬把田自久推回去了。
田自久被别人推着嘴里还骂骂咧咧,铁锤子和田自稳要撵着去打,被田忠良栏挡住了。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就叫他们都回去。众人见没了戏主子,也就陆陆续续地散去了。”
看到这里,谁都会想到,田自久的目的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了。但是,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人的意料——
“田自新见众人散后,这才说开了自己的事情。他说他这次要进的地多,千万请我给他照顾的好一点。
对于田自新的事,我本来是有考虑的。他家六个人要进一千多斤产量,这次如果再不重点照顾的话,那以后确实难得过。但我把自己的意见没说,只是问他想要哪一块地。他说:
‘田自贵退前坡那两亩地能不能给我?’
我没有给他表态,‘你说到这儿,下来我们再研究嘛!’
‘你们啥时候开会公布呢?’他追问着。
‘原来准备的是今晚,还没有最后确定。’我继续给他拖,不说断决话。
‘那我先把你们背笼拿回去用一下。’他说完也不待我答话,就把背笼挎在肩上走了。”
当我们看到这种结局时,谁都会想到,田自久的目的是无论如何也达不到了。但是,下来的事情却出乎人的意料——
“……
我心烦意乱,一个人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只听老远传来田忠良的声音:‘自新,你背个背笼做啥呢?’
田自新回答说:‘这是我借自智家的背笼,去给他还嘛。’
还背笼?他刚借去又来还?田自新搞得是什么名堂?当我对这几个问题还没有思索清的时候,田自新已经到了门口,他背着背笼,上面还盖着一个草帽。
他没等我招呼,就把背笼放在地上,揭开了草帽。我一看上面是一个大纸包,下面一个塑料壶装着十斤酒,酒壶上面放着两块腊肉,还有一个小布袋装着大约十斤米。他把纸包拆开,先拿出两条‘七里香’的烟放在一边。我明白,这可能是他拿的。他又把另两条‘大雁塔’烟提出来说:‘这是自久的一点意思。’
田自久的意思?要知道,当时抽烟有一句顺口溜:县上干部‘大雁塔’,区上干部‘一角八’(这里指的是一角八分钱一盒的宝成牌香烟),公社干部‘满山跑’(这是指一角钱一盒的羊群牌香烟),大队干部‘吹喇叭’(就是用废纸卷旱烟,前大后小,形似喇叭)。这三元钱一条的大雁塔香烟连公社的领导们都抽不起,现在田自久把我‘抬举’到了县上领导的位置,一次就给我买了两条,他这样搞是什么意思?
田自新见我没有搭腔,就急忙解释说:‘我回去以后就把自久美美地收拾了一顿,他就不该和你吵嘛!他被我指教了以后,也知道自己错了,就是不好意思来见你,托我给你说一下:千万请你在分地的时候照顾一下。’(语言直接、简捷,明确了自己送礼的来意,符合农村人的说话方式)。
‘自新哥,你把他的烟给拿回去。你给他说:他的事我没办法!’(开始推脱,一是坚持政策,二是发泄情绪)。
我的好兄弟,伸手不打笑脸人,你咋能说叫我拿回去的话呢?再说,不是我贬低自久的话,他平常是门神老爷的沟子——薄的跟纸一样,根本没有给谁买过东西。今天给你买了几盒烟,就像扳断了他的几根勒子骨,心疼死了,他也确实没有别的办法来表示自己悔改的意思了,请你体谅一下嘛!兄弟,过去人常说:只有个千百年的家门,没有个千百年的亲戚。有这话么?’(第一问,套近乎,圆滑之极。)
‘嗯,有。’我点头承认。
‘虽然说,隔层纱,到底差。但我们弟兄俩根本不在乎隔纱不隔纱的事情,也不存在差不差的问题。哎,兄弟,我说的对不对呢?’(第二问,再套近乎,语气紧逼。)
‘对!’我无言辩驳。
‘咱们弟兄之间虽然不是一娘生,但你见我面不喊哥不说话,我见你面不喊兄弟不搭腔,你能看得起我这个没用处的哥,我也很中意你这个兄弟。哎,兄弟,我说的这话是事实吧?’(这个近乎套得太厉害了,已经由被动转向了主动。)
‘是的,我们的关系确实不错。’我只有顺着他的话说。
‘古言说:不怕生得亲,单怕叫得亲。这事呀,兄弟你有权办,我就是赖死赖活都要请你呢!’(用一句古言,一下子把对方逼到了墙角,稳操胜券地替对方说出了自己的结论!)
‘你把话说到这儿,那我就说不成了,你的地先按你的意见给分(顺从了)。至于自久,人家是有职业的人,他眼里还能看得起我这个农民?我真的没办法,你叫他找别人去!(对田自久的事仍然推)’
‘兄弟,咱们队上的事情谁不知道?我说一句不是挑拨你们干部之间关系的话,你也甭见怪:宋成玉虽然是个支部副书记,他说的话你高兴时能听一句;不高兴的时候,你把他说的话也没有当个啥,还不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大队长是你二哥,他能不听你的?一队又没有队长,你就是眨巴眼望太阳——一手遮天,你在队上说话就是能一语定乾坤,谁不知道?你叫自久找别人,那不是一军把他将死?好兄弟,这事情找别人还不如不找呢!要不这样的:叫自久给你认个错,行不?’(这段话太厉害了!用的是既捧,又挑拨,用挑拨的手段达到捧的真意,使对方防不胜防,更不用说初涉官场的年轻人了!)
‘不是给我认错,是给评议组认错,给群众认错!’
‘是是,给大家认错。不管给谁认错,他这个错总是非认不可的!’(心里虽然不服气,但达到了效果,语气又软下来了,张弛拿捏的特准。)
‘你说话不要气哼哼的不服气!你也知道,我们这院子里一声狗叫都有人要撵着看个热闹,他到我屋里来大吵大闹,是个啥影响?我好坏是个大队干部,以后说话还有谁听呢?’(第一次反问)
‘对,对!’(高兴了)
‘就是我不当干部,你说,以前在我们这大队里谁敢到我屋里来吵过?他把我不当个啥那是小事,还骂公社,哼,这不是寻着挨瞎打么?辛主任在这儿驻队呢,这会儿正在给三队帮忙评产,他知道了还有你们自久的好果子吃?’(第二问。)
‘是的,是的。你甭和他一样。’(真假情意参半)
‘另外,自久和我吵了半天,这些大家都是知道的,我现在又拧转身去给他帮忙办事情,别人要么说他把我压住了,再就是要骂我是个大肉头,软骨头。你想,是不是这个理呢?’(第三问。)
田自新点了点头,闷了半天不说话。(无语胜有语)
我见他那难堪的样子,心里却又不忍起来。又想起田自久毕竟是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如果我这次不给他分地,那就结下一辈子的死仇了,何苦呢?再者,田自久现在已经是拿工资的,说不定哪一天人家转到公社去工作了,那时他再利用职权来整我咋办?于是,就又给他提醒了一句:
‘自久那事也不是百分之百办不成,关键是要看他的态度呢!’
他见我话有转机,就把拿来的东西给我提到了里屋,转出来说:‘兄弟,只要你给办了,你咋说咋好,反正你看在我这个没用哥的薄面子上,给他把事情办了,我领情!’
……”
至此,田自新把两件事情都办成了!
从这段对话里我们看到,田自新在要求给自己分地时用的是进攻的语气,提出了三问;要求给自己兄弟办事的时候用的是被动的语气,答了三问。第一个三问,因为他的事情是正义的,土地非给分不可,只是远近和好坏之区别,所以他明里是套近乎,实际用咄咄逼人的语言使田自智表了态。第二个三问看起来是田自智问田自新,实质这些问都是由田自新引出来的。因为田自新要给自己的兄弟办事,但是事情是非正义的,他就用吹捧、挑拨继之是出主意的办法,引来了田自智的三问,自己做了形似顺从的三答。这三答,看似顺从,用满足虚荣好胜心的方法,牵着田自智走,把一个好端端坚持原则的年轻干部拉到了自己的怀里,干起了违反政策的事。
好狡猾的田自新!
从两分法来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应该警惕田自新这样的人,防止他们在人们不知不觉时毁掉了我们的干部。但是,田自新毕竟是小说里面的人物,他的说话艺术还是有我们的借鉴之处。
我们继续看田自贵和何爱花家务夫妻之间的对话和处理事情:
“饭后,我独自一人到了田自贵家。田自贵还没回来,我和何爱花扯了一会儿闲话之后,就笑了笑说:‘嫂子,你今天咋发那么大的泼?说泼妇,你可算名副其实了!’
她也笑了:‘你看么,他自智叔,狗日的钟耀,那实实在在是个狗子烤火——不沾人气的东西!他说我们娃是多余的,叫我把娃子饿死算球了,你看这话气死人不?’
正当我要向他说明工作组的意见时,田自贵回来了。他一进门就接过何爱花怀里的娃子说:‘来人了嘛,你咋不给找烟呢?’
‘我不抽烟的人,就把这事给忘了。’何爱花边说边进屋找烟去了。
田自贵坐下笑了笑说:‘老弟,你是来找麻达的吧?’
‘看自贵哥说的,咱们弟兄俩么,我能找你啥麻达呢?’我边说边递给了他一根烟。
‘说找麻达是开玩笑。我回来走到路上就遇见你二哥了,他在那里专门等我,给我把事情说了个根根到头。他意思还害怕我和你‘撑’起来呢,看这说的不是见外话?’
‘是的,自贵哥,嫂子一个妇女,说话没高没低,骂了钟耀。你是个男子汉,看这事咋办呢?’
‘咋办?昨天晚上从你那里回来我就想:这事还真硬顶不得,所以今天就躲了一下。嘿嘿,现在还是那句话,听你的!’他瞧见媳妇拿着烟出来了,就逗她说:‘看你这个怂女人,叫你出去躲一下,你装硬汉子不躲,还敢打公社干部。闯这么大的祸,咋得了?’
何爱花边给我们发烟边说:‘咋了?他说要把我们娃饿死算球子了,说得那都是死儿绝女的话嘛,自己嘴挣下的!呃,他自智叔,钟耀说要咋样和我扯筋呢?’
我装作实实在在地说:‘嗯,听说他们要给公社领导汇报,把你做个娃样子,拉到各大队去游队斗争呢!’
没想到这下倒吓住了何爱花,她的脸立时黑红起来,忙问田自贵:‘真的?那咋搞?’
田自贵扑哧一下笑了起来:‘看你平常在屋里横一丈,竖八尺的,叫去游队挨一回斗争也好,我没意见!’
何爱花真的急了,转而向我求救道:‘他自智叔,咱们虽然是嫂叔关系,可和姐弟也没有啥区别。真的叫我去游队,还要挨斗争,你脸上也不好看呀!尽管咋样,这事还得靠你给转个弯子,我领情,田自贵也领你的情!’
‘你们真能听我的,那就说了。’我看玩笑也开得差不多了,就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叫何爱花先在家,田自贵和我一起去向钟耀道歉。
何爱花听了以后,只是略显羞涩地瞅着田自贵直笑。田自贵故意没好气地说:‘你还有脸笑呢,一天死守到屋里。这一下好,闯了祸却叫我去丢脸说好话!’
何爱花扬着脸道:‘你在屋里当家嘛!你咋的,这屋里房子是你的,家具是你的,娃子是你的,女人是你的!呃,你说,现在你的女人闯下祸事了,这个摊子你不去收拾叫谁去收?你不去收摊子了别人笑话你田自贵嘛,真的与我姓何的球不相干!’
田自贵听了,哈哈地笑了起来,‘瞎Q了,这样说你不是赖花秃子烂*娃子——一头都没有一头了,在屋里连一样子都没得到?’
何爱花索性笑着指责起了自己的男人:‘我有个啥?我也造孽的苦情,穷的连个野汉子都没有。我要有野汉子了,唉,田自贵,那人家不用我使唤就赶紧去了,还用着将就你这个高鼻子挂尿壶?’
‘哼哼……不要脸!’田自贵边笑骂着边把娃递给了何爱花。
何爱花接过娃子,‘嘿嘿……’地笑着,揭起前襟,掏出白白的N子,一下就塞进了娃子的嘴里。她那得意的神气,就像是做了一件很赢人的事。
田自贵瞅着何爱花的白N子,笑着嘱咐道:‘一会儿炒几个菜,热两壶酒,我和自智把孙部长叫过来坐一会儿。今天晚上结束可能时间要大一些,你掌握时间。’
‘不准叫钟耀!’何爱花叮咛道。
‘人家和孙部长一路来的人,咋能不叫呢?’田自贵笑嘻嘻地反问。
‘你要叫他来,我就不做饭了!’何爱花没有回答丈夫的话,老起脸说起了个人的主张。
‘我说你们女人家,头发长,见识短,看事情就是只看到脚背上!我不过是说一下吗,你就当实际的?真的叫钟耀,你就是去八抬大轿也把人家抬不来。他就是来了,吃你那几口饭还不是从脊梁骨上下去了?’田自贵数落起了自己的媳妇。
‘那你看着办,反正你当家。嘿嘿……’何爱花不再争执了。
看着这甜蜜的两口子,我不由地从内心感到羡慕:田自贵生活在这样舒心的家庭,甭说叫他去说好话,恐怕就是叫去做比这再难十倍的事情他也愿意……”
这才是和睦的家庭呀!
这里,作者采用了大量的对话,使读者如临其境。田自智逗惹嫂子何爱花,这是农村人常见的玩笑语气。田自贵嚷何爱花,这是一种疼爱的语气。何爱花顶田自贵,这是当媳妇活脱脱的“无赖”语气。对话中的三个人——哥哥、嫂嫂、弟弟,在这种环境和语境当中,只能用这些话说的准确,也简练,容易懂。
《变迁》是一部58万字的长篇小说,里面的对话有很多精华。我们只有在学习中才能看到她的动人之处,才能理解里面的深刻含义。
作者简介:
任雪萍,女,现任旬阳市百合花宛有限责任公司经理。
本期编辑:陈羽
责任编辑:肖海娟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