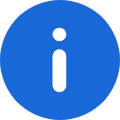那一天之前,我并没有成长在自己的家园,还没有生下来之前,阴阳先生说,我的命硬,不宜落草在盈尔沟。那时候,一个叫火神庙的另外一条山沟里新建了乡村产院,舅舅当着院长,我出生在产院里,而且是产院第一个出生的孩子,后来才知道,我享受着新中国美好生活的过程,上了那个产院史册上的第一页,一直被那个时代的人们谈说着议论着。从产院出来,母亲直接将我抱回家。
没有人送,也没有人接,母亲提着包袱披着明媚的春光,引着我回家了。走过两条沟,翻过一座山,再翻过一座更高的山,一块美丽的盆地就出现在我的面前,那就是我的家园,就是我一生中心中最挂念、口中说得最多、笔下写得最多的一个地名:庙岭。

村庄不大,七八户人家,风景很美,村外有条小河,河边有依依垂柳,家家户户门前有竹园,间或有正在开的粉色的桃花、白色的梨花和红色的杏花,村上全是李姓人家,村外有一块大的土地,叫油坊坪,地里的麦苗青油油的,有一群山鸡排成队在麦田里舞蹈。几十年后,每当我看到外国人跳的芭蕾舞时,就自然地想起那群春天在麦田排成队的山鸡,它们跳着,还发出奇怪的叫声,似乎很开心的样子,听着让人心旷神怡。村庄里没有人,大人小孩一个都没有。母亲没有办法进门,就领着我沿着门前的小河边行走,小河边的路,很窄,只能落下人的脚板,有些路面上,还有塌陷的地方,母亲像电影里的地主老财似的,给我介绍着每一户人家的情况和村庄的山水林田路。走完了南边,她又将我往回带,村子里还是没有人,我家白色楼门上还是那把黑色的铁锁,她又将我带出村庄,往北走,同样说着每一条沟和山的名字,时而还带有来历和传说,北边是开阔地,小河从麦田里划过,流向远方,诗意浓浓,远方又是山,那山是拐弯的,像一条大腿伸了出来,阻隔了小河和土地,山的背后是另一个生产队,母亲说,那是别人的家园,我们就不用去了。我们坐在路边一个土埝上,母亲告诉我,面前最高最长最直的山叫长虫岭,身后长着疙瘩的山叫花术疙瘩,花术疙瘩山上有神庙,我想看到神庙,山太高远了,我只看到坡上的绿树。山上的树多为松树和桦梨树,也有橡树,树上能结人吃的果实有核桃、板栗、桃、杏、李子、樱桃。这些是家果,山上还有野果,山楂、节节果、野樱桃、野桃子、山杏。母亲还说,到了夏天,山上野果很多,有些是不能吃的,吃了人就会死,为什么会死,她没有说清。

有彩蝶在母亲头上抖翅横飞,有蜻蜓在小麦的叶片上弹跳逗乐,有蜜蜂在黄色的花瓣上采蜜,他们会发出不同的叫声,叫声混合在一起,像交响曲,他们的合唱,加深了我对春天的印象。
一直到了下午,太阳快爬上村庄后面的山顶时,夕阳将血红注满山沟,天上的云彩被来临的晚风撕成块状的棉花,平展展地铺在头上,麻雀们开始唱起晚歌,小河中的水,开始变红,村上的所有人,才从村庄北边那个拐弯的山腿处冒了出来,他们一个个精神抖擞的样子,有大人,有小孩,有男人,有女人,虽然是花开的季节,他们的穿着,还是一抹的灰色或者黑色,就连小孩,身上也没彩色的衣服,他们用衣服的颜色,证明着一个时代,一个快乐或者是苦涩的时代。他们是开心的,他们的笑是发自内心的,他们是去大队开全体社员会了,母亲说,每年春天,全大队的人都要开一次隆重的大会,她说这个会,是一个号角,会给人鼓劲,给人力量,给人信心,许多人在寒冷的冬天,扳着指头,算计着日月,他们就等待着开这个大会。她还告诉,在那个会上,人们会听到上面的声音和意思,也知道在这一年里,自己要干什么,怎么干,干到什么程度。
母亲看着门前梁上太阳涂红的山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这一年,庙岭和
国家都会发生许多大事。我拽着她的辫子问她都有什么大事。她说自己说不清,但总会发生的,因为这是新中国,新中国就会发生许多大事,而且都会是好事。我问她什么时候发生,她看着从油坊坪往回走的人们说,他们会知道,你可问你大和你大姐。我问她为什么不能问二姐,她将我从土埝上拉到她怀里说,你二姐念书不多,知道的事少。
我终于等到大姐走到我面前,她身上有一股香味,她看到我,非常高兴,她迈着快乐的脚步从村路上扑向我,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我扯着她的长辫子问她,妈说要发生大事,你能告诉我吗?她亲着我的脸蛋嘿嘿笑得不停说,现在才开春,哪有大事,大事到了冬天才会知道。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大事是人干出来的,春天是做计划的日子,有了计划才能干大事。其实,我知道她在搪塞我,也许她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大事。她只是个上小学的学生。
后来才知道,这一年国家真发生了许多大事,在秋天的时候,中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成功进行导弹核武器试验,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太阳落下山了,月光从门前梁上慢慢地爬起来了,我的记忆之门开启了,就在那一天,我的大脑像摄像机一样,记录了故乡的所有山水,从此,他们再没有被丢失或遗忘,以至现在,就是几年不再去看他们,只要我打开记忆的开关,他们依旧可以随时出现。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要花有花,要树有树,要人有人,要色有色,要声有声。
那一眼春天的山水,从此成了我的故乡,我把它装在行囊里,我走到哪里,他们就跟随我到哪里,我就是漫步在别人的风景中,他们也会从大脑里跳出来,和别人的风景做比较。小时候读课本,知道朝鲜有个三八线,发誓有一天,一定去看一次三八线。几十年后,当我站在三八线上,看到满坡的桦梨树和油松树,还有树林中的落叶及弯弯的小路和我的庙岭十分相似,就是土的颜色也是一模一样的。看到那些似曾相识的风景,不知道为什么,我却哭了,我想起了我的故乡,想起了本家一个叔父在朝鲜战斗的故事。
光阴荏苒,过了几十个春秋,岁月磨砺着故乡的日子,外边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我的庙岭,房舍由土墙换成了砖墙,土路变成了水泥路,山系没有变,田地变得多了杂草,少了庄稼,山林变得更加茂盛,水,滋养着一村的水,就是找不到它们的影子。变化最大的要数人,那些当年陪伴了我们少年时代成长的老人们,大部分去了另一个世界,而新的一代,他们抛弃了山水,想着法儿逃离庙岭,逃不走的,也不在村庄里待,他们像躲避寂寞般,生活在别人的土地上﹣﹣也只能生活在别人的土地上,别人的土地上,有他们永远也赚不够的钱,也只有别人的土地,能给他们生活。我有时已经想不清了,庙岭,在后来人心中,是什么,是养母,还是养子,庙岭生育了后来者,可后来者却不亲它了,远离它了。我自己也是一样的无情,早早逃离了庙岭,我不知道人们的选择是对是错,而我自己却和他们一样做着逃离的选择。
每次回到庙岭,我总是泪眼汪汪,当我行走在那些山水间,外面的世界似乎非常遥远,几乎遥远得让我记不住它们的样子。曾不止一次问过那些逃离了故乡山水的人,你们可曾记住庙岭,他们的回答和我一样,怎能忘怀。
随着年龄的增长,记忆力的减退,当初看到的那一眼山水,却越来越清晰,越来越亲切,越来越向我走近。
人,现代人,经历了岁月磨砺,要生、要活的庙岭人,大都生活在他人的土地上和世界里,有谁认真思考过,只有那方山水才是自己的摇篮,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根。
【作者简介】:

李虎山 陕西省洛南县人,久居西安,中国作协会员,西部散文学会陕西分会主席,商洛市写作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作家,2021年、2023年陕西省主题创作、陕西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创作作家。曾于北京卫戍区服役,担任过乡镇长,报刊杂志总编。
出版长篇小说《鹿池川》《平安》《之间》,中短篇小说集《爱听音乐的狼》,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五十年的眼睛》、长篇报告文学《水润三秦》《庙岭本记》,长篇小说《平安》参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被陕西日报评为读者喜爱的作品并获蒲松龄文学奖,发表作品400万字,获各类文学创作奖50多次。
《平安》入围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之间》刚以出版,就赢得读者喜爱。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