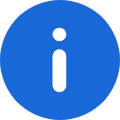大 雪
雪整整下了半个月,像懒散的人做活似的,不紧不慢地下着。山上的树,被雪雕塑成庞大的蘑菇,顶不住压力的,折了,发出一声声脆响,不分昼夜,一声接一声,嘎叭嘎叭,像每年正月初一早晨,庙岭人燃放鞭炮零散的声音,夜里,嘎叭声更清脆,更稠密。

狼饿了,每每到了晚上,站在不同的山头上嚎啕,声音穿越寒冷的气流,挤进每一户柴门。狼一叫,庭院里在桦梨树叶子中睡不着的猪,在圈里惊恐地转着,它们总害怕狼伤害到自己。牛,也无法入睡了,他们用声音提示着同样睡不着的热炕上的男人。一两声狼的叫,并不可怕,个个山头上,群狼在嚎叫,它们的声音,像从云缝里射向村庄的光束,从不同方向,拥向村庄,村庄就胆颤心惊了,猪和牛的恐惧,比人增加了许多。
偶尔,村庄外,狼的叫声停息了,一片死寂,自然不是好兆头,过不了一会儿,村庄里会传出某头猪撕心裂肺的叫声,鸡也会附和着叫起来,一头不幸的猪,成了狼的美食,后半夜,狼不叫了,鸡也不叫了,只有雪落在地上细碎的嚓嚓声。
早晨起来,天地浑然一体,白色涂满了山沟,某户人家的女人,血淋淋的哭声,响彻村庄,牵魂销魄,哭声像命令,将一村人召唤起来,人们看着猪血染红的雪,咬牙切齿,诅咒天,诅咒狼,诅咒男人。
隔天夜里,村庄和沟岔的牛和猪,被人们极不情愿地邀请到人的卧室,它们心神不安地哼哼着,睡在不习惯的炕沿下,拴牛的绳子会拴在柜子的拉手上或柴门的关子上。村庄和沟岔里的人们都那样去做。狼再叫,猪不叫了,鸡不叫了,牛也不哼哼了。
白天,总有一个人,在扫山路上的雪,没有人安排,只要天一亮,他就会主动去地扫雪,他是怀着负罪之心在扫雪,有时,他扫出来的雪,比他人还要高,雪在路边,像战壕,他像电影中挖战壕的人。
清晨,有一帮孩子从“战壕”里经过,孩子们从沟岔先由大人从各个沟岔送到村庄,然后集中送往学校,那个扫雪人,已经把雪扫好了,他要送那些孩子去二里路外的学校,没有一个孩子乐意和他说话。孩子们认为那个扫雪的老人,送他们是应当的,为什么应当,他们说不出理由,习惯成自然。
有些俏皮的孩子,会逃出由雪堆成的巷子,用脚在地上弄出电影里坦克履带的样子,看着身后弯曲的履迹,自己得意地狂笑着,有人要和他比一下,看谁弄得更像,履迹相互交错,没有一个是完整的。雪球成了武器,砸向对方,要么,几个人将一个人压在雪地里,那个人就成了雪人。也有人不喜欢那样的玩法,也是跳到雪地里,用手中的树枝,写上打架人的名字,或者是自己喜欢的,某个女孩的名字。
我总喜欢走在那群孩子的最后边,不参与他们的疯狂,有时,我会从怀里掏出一个有温度的柿子,趁前面的人不注意时,塞在扫雪人的手中。扫雪人是我家的邻居。他接过柿子,不说话,很麻利地将柿子揣进怀里,揣好柿子,会用手擦去头上的汗珠。
走在战壕里,告别了扫雪人,我一直在想,他到底做过什么样的错事,人家总要批斗他,总要在每年的冬天,早早地起来扫雪。有一股雪从空中泼下来,打在我的脸上,我想的问题还没有理清楚,学校到了,秀瑞老师已经开始敲打挂在大队戏楼上的铧犁。
放学后,绕过东沟口那个山峁,我们开始堆雪人了,回家的路上,一路都是雪人。高的低的,男的女的,胖的瘦的,再往前走,就看见了炊烟笼罩的庙岭,家家没有柴禾烧,烟雾就大了。母亲在骂天,父亲也在骂天,所有的大人都在骂天。孩子们没有人骂天的,他们喜欢雪,没有柴烧,似乎与他们没有丝毫关系。
终于有一天,雪停止了,太阳迅猛地从门前沟跳了出来,太阳是笑着出来的,太阳手中似端着火盆出来的,它的脸上有些得意,它像躲猫猫似的,半个月不来看村人,突然间,出现了,还带着火,光照在皮肤上,扎烘烘的。我们说,太阳是把半个月攒起来的光和热,一回拿出来,向村人显示它的威力。
雪在太阳光的照耀下,只用了两天时间,全部化成了水,所有的山上,向下流淌着黄泥水,黄泥水发出了响声,晚上,可以听到一种轰轰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声音,一种令人惧怕的声音。黄泥水填满了所有的小河,冲掉了油坊坪的土地,土地成了黄色的河流,我们说那河流可能是黄河的亲戚,河中有树叶飘飘而下,有树被冲下来,男人们在腰上系了绳索,开始行动了,他们把树拦了下来。有人在打捞柴禾时,被黄泥水冲倒了,又被人拉了出来。
冬天的河变成了夏天的河。
黄泥水中,还漂浮着一只狼,人们把狼也打捞上来,剥了皮,将皮钉在社房平常贴安民告示的墙上,人们向狼宣战了。
这一年,庙岭人损失了不少土地,不是因夏天的暴雨,而是因冬天的大雪,因这场雪,庙岭人收获了不少硬柴禾。
那是五十年来,庙岭下过的最大一场雪,之后再没有下过那么大的雪。
年 画
一直想不通,一字不识的父亲,在1967年那场大雪之后、寒风凛冽的腊月天,山里人日子过得十分恓惶的年月,于什么地方,从什么人手中,买了那么一张好看而喜庆的年画。

那是一张立轴画,画为四尺高,二尺余宽,底色为粉红色,纸上有白色的银粉星星点点的洒在上面,远看,如大姐那年过年时穿的那件棉袄的花饰。粉色的纸上,有五个穿着大红、天蓝、草绿、枣红、金黄色上衣的姑娘,她们除了上衣不同外,下身的裤子全是黑色,每个人脚上穿着一双方口条绒布鞋,头上都扎着统一的长辫子,每张脸都长得粉嘟嘟的,均含着甜美的微笑,五个人手中,皆端着枊条编织的白色的箥篏,画没有任何背景,就单纯的五个人,她们似在进行劳动比赛。
画是父亲买下时就裱好的,画的两边还有对联,对联的内容是:最难风雨故人来,莫放秋日空度过。
腊月三十下午,父亲乐呵呵的,哼着秦腔曲牌,扫完门外的积雪,放了鞭炮,贴了我写的对联,我的对联是用筷子头上缠了棉花沾上锅煤子写上去的,父亲说我的字是狗爪子,但他站在我的字前,脸上却呈现出得意之相。父亲说,历来都是请村上会计水娃哥写春联,从今往后,我们可以不求人了。欣赏完我的狗爪子字,父亲用母亲温好的热水洗了手,将中堂上,原来挂上去的毛主席画像轻轻地取了下来,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年画挂上去。画刚一挂出,引得村上男男女女都来看稀罕。看过的人,都惊叹年画的好。有人说色彩好,有人说年画上的女子们长得好,也有人说我们家的墙好,只有我们家用白土刷过的墙,才配挂这样的年画。
而站在一边一脸笑意的母亲说,是人家画得好,是这年景好,没有好的年景,哪有心情挂这样的年画。
有了好看的年画,我们家的人就多了起来,水也费了,旱烟也费了,听说我们家挂了好的年画,几乎一条沟的人都来看,路过的坟沟人,沟垴子的人都来看年画。
所有人的看,与我的看不同,我不但看画上的五个好看的女子,也在学着画她们。那个年节,我们家到处都是黑色的五个女子,门板上,白墙上,炕头上,水瓮上,面柜上,凡是能画的地方,都被我用不同的黑色画上五个女人。父亲说我画得女人笑的不好看,母亲说我画的女人腰身太粗,大姐说我画的女人身上没有热爱劳动的那股劲,也就是幸福的神韵。村上人不这么说,村上人看了我的字,看了我的画,都吆喝说,不得了了,我们山里要出秀才哟。父亲听后,嘴上说,一个几岁的娃仔,什么秀才呀,说不定将来和咱们一样是个握镢头把修地球的角儿。
背过村人,父母却对我疼爱有加,母亲还把大姐的一件夏季穿过的衣服,给我改成夹袄,用于奖励,在我没有写对联前,母亲是没有这样的计划的。
其实,那时的我,对家人和村人的褒贬,并不在意,我的心思,除了在那五个好看的女人身上,看着她们鲜活好看的眉眼,说不出心中有多么受活,更多的想法是,要真正做一个画家,能画出七彩女人,画出比年画上人多还要好看的女人。
那是我人生中,最初的梦想,也是第一次被艺术感染后产生的想法。
但我的梦想被新年后的运动彻底摧毁了。
元宵节过后,住队干部带着新的政策,急匆匆来到庙岭,他们先挨家挨户地检查春粮,为春耕春播做着准备,紧接着,检查每一个人的思想,检查中,有人发现,我们家的中堂上,没有毛主席的画像,却挂上了年画。这还了得。
父亲被揪了出来,原因是,挂年画的地方,是挂毛主席画像的地方,父亲滋生了资产阶级和封建主义思想,将毛主席的位置让给了五个长得漂亮的女人。父亲被揪到了村人面前,一天一天地接受批斗,一直批斗到父亲从木板凳上摔下来头破血流,不省人事方才罢休。而我们家的年画,却被工作队的队长收缴了,他本来是要烧掉的,大姐不知道采用了什么办法,要回了年画,那张年画一直被大姐保留着,到她出嫁时,才交给父亲。
起先,我是多么地爱那张年画,当我看到父亲接受批判时痛苦的样子,我却对那张年画产生了恨意,恨意甚至延伸到那五个女人身。
有了那样的经历,我对画画,产生了恐惧,就是后来上了几十年学,一上美术课,我就有一种强烈的反应,就会想到父亲被揪斗的情景。
时光浸泡过四十年的岁月,1999年春天,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出版后,我从西安回去为父亲送书,父亲领着几个弟弟正在做砖瓦,准备修房子,父亲告诉我,他计划搬倒老祖先留下的瓦舍,建起楼房。父亲看到我的书,泪眼婆娑,他从一个黑色的粮食瓮里拿出了那张被他用塑料纸,包裹了许多层的年画,将其慢慢展开,将我所带的三本书轻轻地放到那五个女人身上,他向她们合手礼拜,口中念念有词。父亲说,感谢你们了,老古董,是你们让我们家出了秀才,要是没有你们,当年冒着大雪,伴随我从山外到我们家来,启蒙了我的儿子,我们家哪儿能出秀才啊。
礼拜完毕,父亲对几个弟弟说,你哥之所以有点出息,是这幅年画给了他灵性,通过年画的遭遇,使他小小的年纪,领悟到了生活的真谛,他才能写出书来,我当年为什么敢冒那么大的风险,把毛主席老人家从墙上请下来,挂到侧面的墙上,挂上这幅年画,一是我特别喜欢这幅年画,你们看看,他们长得多么像你们死去的大姨和二姨,因为你们的两个姨去世后,你母亲的人生改变了许多,她总想着,有一天她也会早早地死去,她几乎失去了活下去的勇气。二是送画的人给我说,挂上这幅年画,家里会出秀才,我知道他是哄我哩,咱们这样的家庭,咋会出秀才呢?可谁会想到,你大哥看到这幅后,不但喜欢,而且天天照着年画画,虽然他没有成为画家,却出了书,那不也是秀才么。
父亲拜过年画之后,又把年画收藏起来,一直到他去世后,我们再没有见过那张年画。
有一年,我一个搞收藏的战友从北京来看我,我谈到了年画的事,他认为,那张年画一定有收藏价值。我们开车从西安回到老家,翻遍家里所有的东西,也没有找到那张年画,后来村上一个为父亲入殓的老人告诉我,那张年画被藏了起来,藏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作者简介】:

李虎山 陕西省洛南县人,久居西安,中国作协会员,西部散文学会陕西分会主席,商洛市写作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作家,2021年、2023年陕西省主题创作、陕西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创作作家。曾于北京卫戍区服役,担任过乡镇长,报刊杂志总编。
出版长篇小说《鹿池川》《平安》《之间》,中短篇小说集《爱听音乐的狼》,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五十年的眼睛》、长篇报告文学《水润三秦》《庙岭本记》,长篇小说《平安》参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被陕西日报评为读者喜爱的作品并获蒲松龄文学奖,发表作品400万字,获各类文学创作奖50多次。
《平安》入围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之间》刚以出版,就赢得读者喜爱。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