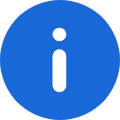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五)
孙成在回家玩了七八天之后,来到田家坪检查联产到劳工作。
那天,他径直来到我家。我叫母亲给他炒了几个菜,谁知他见了之后,愁着脸说:“自智,公社最近要开联产到劳阶段总结会,你们二队现在还没有弄好,咋办呢?”
我本来对他在会上和会后的两样做法就有意见,当时就故意逗他说:“支书都弄不展么,我有球的办法?”
他很着急,在饭桌上立坐不安。见我只是一股劲地劝酒,就没好气地说:“你只会吃、吃!只知道喝、喝!工作搞得那个球样子,叫我咋交差?”
我也没好气地回敬他说:“我一个农民,大不了大队会计不当了,你还能把我这个农民开除了叫去当干部?至于你的事,与我个球不相干,我看你还能舍得把铁饭碗子给摔了?”
“好,好,这是我的事,我去找评议组的人商量!”他放下酒盅,立起身来就走。
我见他确实到了急不可耐的程度,才知道公社对联产到劳工作真实逼得紧。待他走到院坝边上的时候,才慢声细语地说:“孙部长,你转来,我给你看一样东西了再去!”说完就进里屋去取合同书。
待我从里屋出来的时候,只见铁锤子也尾随着孙成进来了。孙成没好气地向我说:“你叫我看啥?”
铁锤子几乎和孙成异口同声:“自智哥,声娃子在洞沟里擀面了!”
我没有回答孙成的话,只是把二队各户的合同书递给他,转过身来问铁锤子:“啥时候?”
孙成一手接过合同书,连翻也没翻,就不高兴地训斥铁锤子:“你这娃,擀面么有个啥子大惊小怪的,还跑来给你自智哥说!你没看我们正忙着吗?一进屋说话就抢死一样地抢!”
我明白孙成是为铁锤子和他抢着说话而生气,也知道他没有听明白铁锤子的话意,当下就解释道:“孙部长,你不知道:有时从山上放树,人在下面跑慢了,树从人身上碾过去,把人带几个滚,就像在案板上擀面一样,我们这里人叫擀面。铁锤子,声娃子不很碍事吧?”
“咋不碍事?”铁锤子绘声绘色地说:“声娃子和自文哥今日一早到国有林去偷树,一人砍了三丈多长一根,嗯——,估计有水桶那么粗的松树。自文哥的树一放就放下来了,声娃子的树在半山坡上插在了一个树疙瘩上,他用杠子把树根子一翘,树向下一窜,窜在了一个斜石茬子上,树顺着石茬子一歪,就把他打倒了,树身子从他肚子上一碾过去,碾着他打了两个滚,骨头倒没断,估计是肠子吃了亏。本来要到你们这儿来请我舅去给看,最后听说舅舅没在屋,又请人到兽医站去把陈医生接来了。”
孙成一边翻看着合同书一边听完了铁锤子的叙述,他拍拍我的肩膀说:“你这个怂东西娃,把我哄得好苦,搞好了就直说么,害得我担一肚子的心!你不知道,这项工作完不成了公社通报批评是小事,还要扣发这个月的工资呢。噢,铁锤子刚说到兽医站接陈医生,他是兽医怎么会看人病?我说田德印也是球疯筋了!”
我回答说:“那——,我们公社卫生院的几个人还不如陈医生,你们社属单位都有哪些鸡子、狗子人才的你不知道?”
孙成被我说的很不好意思,摇摇头说:“球的办法!我有一次感冒了,叫他们给开药,开始我看处方上写的止咳灵一瓶,还只当是几十颗的小瓶呢。等我把钱交了以后拿到手上一看:一千颗!你说这些事情区上不管么,我们公社有啥主意?走,我们都到德印家里去看一下!”
我们几个来到田德印屋里,只见田德声已经躺在床上,疼的脸色煞白。陈医生坐在旁边,瞅着空中吊的葡萄糖瓶子,安慰着围观的人:
“不要紧,不要紧!先给吊两瓶葡萄糖,增加一些营养,然后再吃两副中药,休息一段时间,就没事了,你们放心!”
孙成挤到床前,爬着看了一下田德声的脸,回过头来说道:“陈医生,他这伤最好要去县医院检查一下吧?”
“没事,没事。孙部长,你放心,我刚还给号过脉了呢!”陈医生打着保票。
一瓶葡萄糖没吊完,田德声就把田德印的手拉住说:“哥,你叫陈医生把针给我取了。”
田德印说:“娃,你先叫打么,我又不心疼钱!”
田德声哼了一声,半会儿才说:“我的伤我知道,这是肠子断了,恐怕难的好。算命的也说了,我今年是二十四岁,有个一丈二尺高的门槛子,难翻过去,哪晓得正应在这个事上。”
田德印纠正着兄弟的话,说:“娃,你忘记了,你二十四岁生日上个月已经过了,现在正过二十五岁的日子呢。”
“反正,反正生日才过,时间也不长。”田德声给自己找着倒霉的理由。
“你就是不打针了,我也请几个人把你抬到县上去检查。你放心,陈医生说不碍事!”田德印给田德声宽着心。
田德声把头转向陈医生说:“陈医生,我这伤不是打葡萄糖能好的,你给我把针拔了。我知道,你也尽心了,我也不怪你,你们兽医站就那个条件。”他眼瞅着把针拔掉之后,才又回过头向田德印说道:“哥,我们大人去世的早,是你把我拉扯大的,你也不要再花钱了,让我凭命板去!”说到这里,他猛地有些接不上气了,“我也……不怪你,怪只怪……我们生到这……穷地方,没钱用,离县城又远……”
田德印眼望着自己懂事的兄弟,嘴里翻来覆去地重复着:“不碍事,不碍事……”他一直坐在床边,饭也没吃,水也没喝,不时地用毛巾粘掉田德声脸上的汗水。田德印尽管是如此的用心,一直不眨眼地望着兄弟,但是到底没能打动索命无常那铁石心肠。在熬过一夜之后,天快亮时,他的兄弟还是离世而去了……
田德声虽然属于少年亡者,但田德印还是按照老年亡人的事场子来安排:请有念经的,唱孝歌的,戏房吹喇叭的。他眼泪汪汪地向大家说:他们弟兄俩老早就离了娘老子,德声自小就跟着他受罪。活着没享到福,这就当生在穷家庭还能说过去,亏心的是连个后代都没有留下,更不用说活够六十岁花甲子的一世人了,他一想到这些心里就难受得要命。他要请念经的好好把兄弟超度一下,给兄弟多烧一些纸钱,以使他到了阴间能出人头地,有钱用,享几天福。他最后说,思来想去,要提高事面子上档次,就得请一个有身份的人来管事,这样才能对得起兄弟。
于是,他专意拿了四样礼到田德远家,请田德远的家人给捎信,叫他回来当过事上总管。
对于田德印这样安排,没有一个人谈论不是的。我们一个院子如果谁家有事,大家都是一齐来动手帮忙,田德远自然很快就回来了。我作为侄辈,按常规来说本应该安排在劈柴,扫地,或者端盘的杂务之类岗位上,但这次田德远按照田德印的吩咐,对我的“工作”安排却作了破格的“提拔”,叫我当上了支客。需知,红白喜事上,一个总管,紧接的职位就是几个支客,下来是管库房的己亲,最后才是一般帮忙的。总管只掌握过事的总盘子,不搞什么具体事务,哪个岗位出现特殊事情缺人了,他负责给调剂替补的人,有时自己也顶着干。支客顾名思义就是支应客人,事务比较具体,上管着主东吃喝,下管着所有来客的席次安排,还肩负着安排帮忙人活路轻重的搭配工作。更为实惠的是能在库房里领一些饼干、罐头和烟酒一类的东西,所领的这些实物在给客人发过之后都有多余的,这多余的一部分当然没有谁傻着去上交,一般搞了自我慰劳,也可以送给相好的做一些私人人情,有时还能在神不知鬼不觉时揣上几片饼干回家哄娃子。反正,只要你当上了支客,灵活地运用自己手中握有的一些“实权”,一门心思地钻,那多少还是能图一点利的,最起码不会亏着自己,这职事有时比单位的副职还厉害。
我第一次担任支客职务,也不知道如何去履职。还好,田德远是个聪明人,他明知道我占这个位置不合适,但农村过事你好坏总要占一样职事呀!如果一样都不占,那谁家门前都没挂无事牌子,遇到你家红白喜事了谁来帮忙促这个场子呢?田德远不愧是一个圆滑的人,他就索性做个人情,安排叫我专职接待外队干部和公社的领导,这下算是给我明确了职责。在农村人的眼里,干部比百姓的地位要高,面子要大,这个规矩人人皆知。以此推理,接待干部的支客,必然要比其他支客的地位高一些。田德远这么做,无形当中把我的身价又抬高了半个级别,已经等同于单位里的一个常务副职了!
这样的安排却不是胡整?田德印一个小小的老百姓,在官场上并没有什么交往,家里出现了少年亡者,又不是老父老母,这样的忧事除开本大队几个干部能来看一下之外,外大队的干部谁来看他?田德远也不是不知道田德印有多大多粗,在人面子上还说叫我招呼来上事的公社干部,这不明摆着叫我玩嘛!
但是,世上的事就有一些千奇百怪的,那些看似没有影子的事情,有时却出现了!我在事场子上看别人都在忙碌着,自己却没事干,就只好回家睡觉。天过晌午,我在睡梦当中被人摇醒,睁眼一看是公社的辛国余。他向我问了一些工作方面的情况,我都汇报得清清楚楚。汇报之后,我正暗自庆幸自己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满想着辛主任肯定要表扬我几句。没想到,他问完了工作之后,不但没有肯定我的成绩,而且还一脸怒色地问我:
“你们队上的田自平结婚是咋回事?”
“田自平结婚?结啥婚?人家不是把媳妇都引到屋里去了嘛!”我装着轻松地回答。
这时,孙成听说公社领导来了,也赶来招呼。他先给辛国余发了一支烟,接着问道:“辛主任要来,咋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辛国余并没有理会孙成的讨好,继续向我问道:“田自平够没够法定结婚的年龄?”
我回答说:“结婚年龄要够二十二岁嘛!他今年才二十一岁,年龄当然不够。”
“那你为什么要给他开结婚证明呢?”
“我也没开证明,他们结没结婚我不知道。”
“你要说好,这事情的后果要负责任呢!”
我继续佯装道:“我只看见田自平接媳妇,至于领不领结婚证是你们公社的事。噢,领结婚证还要大队的证明?”
“糊涂,简直是糊涂!”辛国余高声地批评起来,“你这个大队会计是咋当的,连个领结婚证要证明的事你都不知道?年龄没够开结婚证明是违法行为,你为啥连这点关都把不住?”
受到辛国余的批评,我当时虽然有一些委屈,但心里同时有一丝高兴。说实在的,田自平仗着他爸在公社供销社当收购员,做事把我确实没放在眼里。他接媳妇那天,还故意把结婚证摆到桌子上叫大家看。当时田自贵喊着他的绰号问:“猴子,你是不是请自智给帮忙赚腾的?”他故意高声地回答:“我办这事,根本没用大队上的人插手!”一圈围着的人立时就向我投来了鄙视的眼色,那意思很明显:“看,你也就那点能耐,办一些有关系的事情了谁能用上你!”我当时被他说得很无趣,坐了一会儿就灰溜溜地走了……
现在公社领导对我批评的越扎实,追得越紧,说明越有“猴子”的好果子吃。哼,看着!我故意不作声。
孙成见我不说话,还以为我挨批评受到了委屈,忙替我说话:“辛主任,这事是钟耀一手办的。自智根本没有插手,你把人家批评冤枉了!”
“钟耀?钟耀不是公社团委书记么?他办事难道不在会上汇报,还能把你们领导瞒着?”我故意紧顶了一句。
“哼!他办这事还敢上会?如果有哪一个领导知道也就好了!这个娃,我们原来还想把他当苗子培养呢,叫他当个团支部书记,还兼文书,谁知道是这样的一个货色!”辛国余也觉得有些歉意。他转过来详细地问了我们联产到劳的具体做法,高度地赞扬了我的工作成绩,顺带把孙成也表扬了几句。末了,他掏出一元钱给我说:“自智,你在当支客呢,公鸡头上长的肉——大小也算是有个冠(官)儿呢。我既然来了,不去上个份子,那就太不给你面子了!”
我推让道:“辛主任,你和田德印又没啥交情,咋能叫你破费呢?再说,一般搭份子也只有五毛钱,你给的也太多了!”
“你这娃,辛主任把话都说出来了,难道还能收回去?这事明显是为了给你装面子嘛,还推让?来,给我也搭上!”孙成说着也掏出了一元钱。
我接过了钱。在我把两个公社干部的钱拿到礼房时,只见田德印正在那里低声地哭。当他听到接礼的喊“辛主任、孙部长礼金各一块”时,当下就止住了哭声,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他清楚,凭他田德印哪有这么大的春风,死了一个名不见爵的兄弟,还能劳驾公社的领导来给上份子?当下也不管那几个正找他商量借酒借肉的人了,急忙找到田德远,轻言细语地提出了自己的商量意见:
“德远哥,你看公社领导都来了,这叫人咋受得起呢?人是个啥?钱又是个啥?人家能来看一下,是千个菩萨朝着哪个菩萨脸上看的?还不是跟自智熟,看自智在当支客嘛!我们这事情,就是公社领导空手能来看一下,都领当不起哟,还不说害得人家花钱!”
“是的,是的!”田德远连连点头。
“我想我们应该另外再弄一桌子比较像样一点的菜,众人喝的柿子酒就不上桌子了,到代销店去买两瓶好一点的酒,请你和自智单独把人家陪一下。我没想到辛主任和孙部长也能来看一下,还能给上个份子,这个礼簿子可真是有保存的价值呢!以后娃子们长大了要叫他们记住,长远地传下去,嘿嘿……”田德印说着说着,脸上竟然挂着两行泪笑了起来。那神情,好像公社领导一来上份子,他的忧事一下子就变成了喜事似地。
田德远自然也很高兴,他两手一拍,高兴的脑袋直点,“行,这事你放心,我保险给安排好!”
过事的晒席棚底一长溜子摆了三张桌子,田德远把辛国余坐的席位安排在居中一桌。因为他是公社领导,属于官方人,田德远就没有按本地老传统给安排席位,特意安排了一桌官席的坐法:上方坐着辛国余和孙成,左方由我紧挨辛国余坐着,再挨身是田自荣,右方由他自己和我二哥相陪。本来下方还可以再坐两个人,但田德远叫空着,他说官席就是这样一种坐法。他知道我看不起宋成玉,两位公社领导对他也不感兴趣,就以官席人满为借口,没有安排宋成玉来陪。
辛国余初开始说田德印家里死了人,还没有上坡就去喝酒,不合适,死活不愿意去。但他挡不住田德印一个头又一个头地磕,经不住几个管事的一再拉扯,加之孙成又在一旁不停地劝说,最后拗不过,到底还是去了。
我们坐在席上以后,田德印先是对我们一桌人恭恭敬敬地磕了四个头,起来作揖时,田德远就伸手拦挡道:“好,四礼道谢,好了!”田德印殷勤地笑着,给上席两个领导先筛了四杯,待他们喝过之后,又端起盅子再陪四杯,然后依次给我们每人敬了四杯酒,又磕了四个头,这才转身去给其他桌子上的人敬酒。
田德印走了之后,宋成玉拿着另一桌的黑土巴酒壶来敬酒。宋成玉知道瓶子里的酒没有他的份儿,就先拿起我们桌子上的酒瓶给辛国余和孙成筛了两杯,算是敬酒,待两位领导喝了之后,又给每人筛了一杯,然后换过泥巴酒壶给自己筛了一杯,从辛国余跟前开始碰杯。他给公社两位领导碰过杯后,又和桌子上剩下的人共同端了两杯,这才笑眯眯地回到自己刚才坐的桌子上去了。那样子,不亚于拾破烂的捡了一个银碗,很是得意。
在事上帮忙的其他几位队干部,见宋成玉给公社干部敬过了酒,也都不甘落后,开始围到了我们这个桌子边,挨次地敬起酒来了。田自弟也想凑热闹,但他怕领导不给面子,伤了自尊心,就先从我跟前敬起。和我喝过之后,他把我胳膊一碰,又向辛国余努了努嘴,意思是请我先给通融一下。我也不好推辞,就端了一杯酒,站起来笑着说:
“辛主任,自弟哥想给你敬酒,也是一番好意。你俩喝着不热闹,来,我陪一下!”
辛国余当时也有些醉意,就没有多说,端起酒杯,一饮而尽。田德远坐在旁边见领导的兴致很好,便向田德印伸出了两个手指头,向外一指,那意思叫他到代销店去再取两瓶酒。田德印一边点头,一边拧身就到代销店去。他不一会儿就拿来了三瓶太白酒,笑吟吟地蹲在我们的桌子上。
这一天,我们桌子上本大队的四个人,陪着公社的两位领导把五瓶子酒喝了个底朝天,一个个都喝得东倒西歪。田自荣的酒量差一些,刚离桌子就一口吐在给田德声烧的火纸上。
“唉,这成个啥样子嘛……”在场的人都愤愤不满地议论起来……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八章:联产到劳的时候】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
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责任编辑:肖海娟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