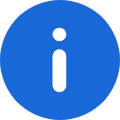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二)
集资办学运动月伴随着学雷锋活动,声势浩大。这一个运动月刚过,计划生育运动月又来了。区上这一次催得比任何时候都紧,茬子比任何时候都要硬。这次工作和以前最显著的区别是要求先把声势再造大,宣传活动要搞得轰轰烈烈。
由于运动月一个接一个地搞,以前把该写标语的地方已经写满了,现在再要求写标语只有在原有的标语后面和路边的石板上续写。乡村干部只有积极配合,抽出专人搞宣传,这样就使沿路都刷满了如何把计划生育搞彻底的标语。专职工作队用横幅布写着“誓死打胜计划生育的硬仗!”使人看到这些真是英勇悲壮!
这时我们区上的书记在公社改成乡之后已经换到第三个了。新来的书记是有名的点子领导,他来到后搞计划生育主要是先从干部职工身上开刀,然后以干部职工的行动去带动农民。他把五个乡的书记乡长召集起来开会,散会后就把有超生的三个乡长、两个书记留下没叫走,名义上是办学习班,搞培训,实质上和软禁差不多。他叫乡干部给留下的书记和乡长的妻子捎信:迅速到计划生育服务站去做手术!我当时听到这些消息后,很有些兔死狐悲的感觉,因为区上留下的这几个乡上领导,其中有两个是我高中时期的同学。好在后来听说区上只叫他们的妻子做了结扎手术,没有给什么纪律处分,这倒使人心里还有了一些宽慰。
区上都这样硬做,各乡哪里还敢怠慢?一时间各单位、各系统从上到下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做手术之势。我们冷水乡的行政部门只有团委书记钟耀是超生二胎的,单位给他放了假,名义上说要求回家去引媳妇把手术一做就了事,实际是叫他不做手术就不要来上班。综合厂里有几个生育二胎的,也够不上什么行政处分,只是被逼着去做了手术。最惨的就是教育系统了,公办教师没有超生的,倒是十四个民办教师就有六个人超生了二胎。区上文教组在查出人员,列出名单之后,由组长张吉带来了几个工作人员,把我叫到乡中心辅导站,商量看这事咋办?
“咋办?你们说咋办?”我想先摸清他们的底牌。
“我们想是这样的,”张吉恨恨地说:“教育队伍里出现了这么多超生的人,真是一些败类,他们害得我在区上受了几次批评!这次一定要来硬一些,彻底扭转这个被动局面!叫他们先去做手术,至于行政处理的事情等下一步再说。”
我见他把话没有说清楚,就同他商量道:“张组长,要说罚他们的款都没话可说。就目前来看,鉴于我们这里人才奇缺的现实,你看是不是从组织处理方面稍微放宽一点?”
张吉笑了起来,“老弟,我知道你的心情是好的,你是本乡人,不好下手。这次你只负责叫他们做手术,其他的事你就不要管了,我会把你的话作以考虑的!”
这是实情,他也不敢说不处理的话。在计划生育政策面前,谁能包得住?这有连带责任的事情,谁想在这方面去砸自己的饭碗子呢?
我依照和文教组商量的方案,当晚就在广播上通知几个超生的民办教师,要求他们在明天中午十二点钟以前赶到乡政府开会。
第二天,几个被通知开会的民办教师陆陆续续地来了。我准备好了会上应学习的材料,刚要到会议室去时,田自久一脚跨进了我的办公室。他含着泪,用袖头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声音哽咽地说:
“自智,我今天恐怕不能参加会议了!”
“咋搞的?”我感到很惊奇。
“早上,”他用手背抹了抹流出来的泪水,“早上,我从家里走的时候给何桂知说,乡上通知我们几个民办教师开会,肯定是我们违反了计划生育的事,叫去做手术。她开始说不准我来,我就向她解释说:‘这只是我猜测的嘛,乡上又没有明显通知叫做啥,只是通知叫开会,我咋能不去呢?’她就哭着说:‘我哪怕是去死呢,也不愿去挨这上一刀’……”
我听了也直想笑,“结扎这是一个最小的手术嘛,她咋能吓成这个样子呢?”
“就是嘛,我给她死活都说不清!她听别人说,结扎在掏管的时候疼得要命,手术过后还不能动,要睡半个月。我走时她抱住我的腿,嚎天吼地的,我实在没办法,打了她两个耳巴子才走脱的。刚才田自刚把我撵到乡上给我说,何桂知上吊了!”
危言耸听!我为他编得这谎言好笑:不想去做手术就说不去嘛,干嘛要编这些谎话来哄人呢?但当时又不好当面说破,就给他倒了一杯水,“咋能打她呢,你也是不该!先喝水,一会儿把会开了再回去看一下。”
“不!”他带着哭腔说:“我马上就回去,看能不能把她抢救转来!”
“那——”我一想,万一这事是真的,别人还会说我不近人情呢,“你回去看一下也好。你叫田自刚到我这里来,我把情况问一下,也好给其他的领导作以汇报。”
田自久走了,田自刚就来给我把情况说了个详细:“自久早上走,他的媳妇和他吵,他打了媳妇也是真的。”
“真的?”我忙追问,这说明田自久没有说谎。
“自久走后,”田自刚声音有些哽咽,“何桂知心慌的满院子跑,不久她提个笼子给自新哥家里的刘嫂子说,她要去寻猪草。上坡以后,她从前梁到后坡一味地跑,回来时笼子里只装了一大把猪草,一进到屋里就把门一关。刘嫂子开始还没在意,过了多长时间她一思索:何桂知白天是不睡觉的呀,她把门关了这半天做啥呢?于是,她就去拍着门喊,喊了半天没人答应。她一想不对劲儿,就急忙叫自新哥来把门踢开,进屋一看,天啊!何桂知在堂屋的楼枕上吊着,她那半岁的儿子还在床上睡着,睁大两只眼睛看着他妈!自新哥赶紧把人放下来,用膝盖顶住沟门子,——他怕一放屁就漏底了,那样人也救不回来了。刘嫂子就急忙喊我去帮忙,叫我把自久撵回去。自久他们一路几个人走得慢,我撵到离乡政府不远就撵上了……”
“人咋样?能抢救转来不?”我急忙问。
“不行了,舌头都伸得老长了!我们听到喊声进去时,看见自新哥把何桂知的头抱着,正嘴对嘴地咂。刘嫂抱着自久的娃子,这小东西也不懂事,看着他妈睡在地上,还在刘嫂子怀里高兴的直窜,‘咯咯……’地笑个不停。惨啊,自久现在两个娃,大的不到三岁,小的还不到一岁……”田自刚说着眼泪长流。
惨,惨啊!我不由地也流出了泪,深深地后悔起自己工作的失误。如果我们当时能上门去做好工作,向何桂知解释一下结扎不是那么可怕的,消除她的思想顾虑,或许她会顺顺当当地去做手术,也或许她做了手术以后还会感激我们。但是,我为什么就没有这样做呢?我为什么要在广播上通知他们来开会呢?叫男的来开会,男的工作做通了,而要做结扎手术的是女方啊!女方这一层的工作,我为什么没有去考虑呢?在广播上通知田自久他们开会,这在何桂知听来是什么感觉,和给她不断发的催命符有什么区别呢?从这一点来说,何桂知的死,我能完全推脱责任吗?一连串的问题一股脑地向我涌来,我受不住了,只能任从悔恨和愧疚的泪水止不住地流……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十九章:无法负起的责任】(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陈羽
责任编辑:刘萧娇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