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献给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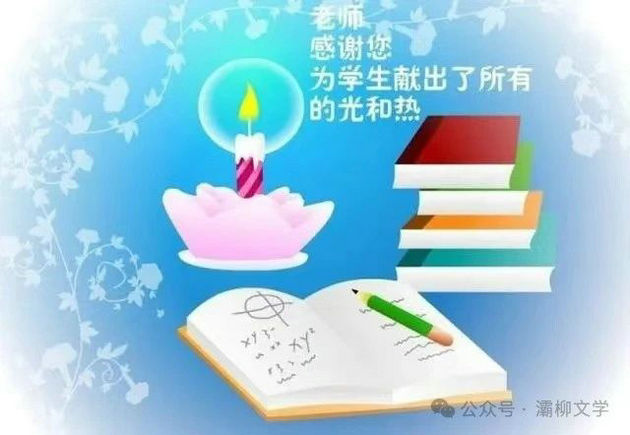
在我的求学和执教生涯中,曾经得到过许多老师的教诲和指点。这些老师对我的人生经历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也使我时常在夜深人静时回忆起和他们在一起时的点点滴滴,于是,一种深深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就会从心底油然而生。
一年一度的教师节马上就要来了,许许多多熟悉的亲切的面容像过电影一样在我眼前浮现。而在众多的师长中,有一位既没给我上过课也没有和我共过事的老师,刹那间占据了我的脑海,他的音容相貌以及和他短暂相处的情景也历历在目。他的名字叫蒋维礼,我和他的相识缘于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和我同在一所学校工作)。在这个全国教师共同欢庆自己的节日里,我把他的故事记录下来分享给各位朋友,也算是我对蒋老师以及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一点追忆。
一九八二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陕北吴堡县的一个乡村中学——吴堡县郭家沟中学(因为那里曾经是一座寺院,叫太平寺,所以,当地人习惯上也把它叫做太平寺中学)教学。郭家沟中学是吴堡县当时所有中学中条件最差的。这个学校不仅离县城很远,而且山大沟深,交通不便,连班车也没有,人们进城只能靠11号。学校的设施也非常简陋,生活条件更是谈不上。所以,每年分配来的教师很少愿意去那里任教。当时的县教育局长说为了加强郭家沟中学的师资力量,就把当年我这个唯一的本科毕业生分到了这个“太平市”中学。
时间过得飞快,很快几个月就过去了。这时候,又一批新人员被充实到了各学校。这批新人员都是按照当时政策,落实知识分子待遇,照顾性的招收的。其中有一位叫蒋俊的就被安排到了我所在的郭家沟中学。
蒋俊当时很年轻,应该还不到二十岁。记得一次在会议室看电视,当时电视正在播放体育比赛节目,其中有撑杆跳高这个项目。小蒋不认识撑字,总是读成掌杆跳高。电视节目结束后,同事们纷纷离开会议室回自己办公室(陕北老师都是每人一孔窑洞,办公室兼宿舍)休息去了。这时候我悄悄把小蒋叫住,对他说,那个项目不叫掌杆跳高,而是叫撑杆跳高。一时间,小蒋似乎有些尴尬,但是眼睛里却露出感激的眼神。自此以后,他和我走的越来越近,没事时总喜欢粘着我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熟络,有时遇到周末也会结伴进城,他的家在吴堡县城,我回家也必须经过吴堡县城。两人一路上边走边聊,六十里山路不知不觉中就到了。
转眼间,一学期就结束了。一九八三年的春节在隆重的鞭炮声中渐渐离我们越来越远。
新学期开始后,蒋俊没有按时来学校。大概开学后一周左右,他容光焕发地走进了我的宿舍。看到他时,着实使我吃了一惊,因为两个月没见,他的精神面貌几乎完全不一样了。身上焕发着一种自信,满足,给人一种曾经沧海的感觉。我不由得问他,你寒假做甚去了?他两眼放光地说道,回上海去了。什么?回上海?你不是地地道道的吴堡人氏吗?怎么说回上海了呢?他后面的话更加让我吃惊到眼珠子都要蹦出来了。我父亲本来是上海人,我的爷爷是蒋学楷,我二爷爷是蒋学模。
哎呀,我的个妈呀!这两个如雷贯耳的名字把我震惊到几乎要坐到地上了。蒋学楷,蒋学模,这都是神一般的存在啊!大师,真正的大师!朋友们可以百度一下,百度是这样介绍这弟兄俩的:
蒋学楷,字涵豪,1909年4月13日生于慈溪观城镇卫前蒋家后房(今观海卫镇蒋家桥村)。1927年毕业于上海澄衷中学,1931年毕业于上海劳动大学社会学系。蒋学楷先生是一位英勇的文化斗士和翻译家,曾任上海国际贸易局专员、复旦大学《文摘》编委、香港《财政评论》编译、香港大时代书局经理。1942年被日军枪杀于香港,时年33岁。
蒋学楷所翻译的美国约翰·根室的《亚洲内幕》《欧洲内幕》《拉丁美洲内幕》三本书,在抗日战争前后有广泛的影响。香港大时代书局当时是一个进步书店,在蒋学楷任经理期间,出版了抨击法西斯在“二战”期间罪行的多本译著,为日军所忌。1942年重藤宪文在广州发现香港《亚洲内幕》(文摘社)杂志上登有号召亚洲各国人民奋起抗日的文章,就赶到香港,伙同日军香港宪兵队队长野间助之贤,出动宪兵在香港九龙四处搜查,野间派出宪兵对《亚洲内幕》人员严加侦察,发现有很多文章是爱国人士、《亚洲内幕》编辑蒋学楷所写,就派香港宪兵对蒋学楷立案侦察。野间派出的宪兵在九龙避风塘发现了蒋学楷,只见他坐船而来,日本宪兵就在蒋学楷后面跟踪监视,请示野间助之贤后,日本宪兵在蒋学楷登舟而去时,将其开枪打死。
蒋学楷在短暂的一生中,著作、译作较多,包括创作短篇小说集《留痕》,翻译《狐狸的故事》《青春》《政治浅说》《陶立德博士》(1931年译)等。蒋学楷汉译的康拉德的《青春》(上海南华图书局出版)是第一本在中国出版面市的的康拉德译著。
蒋学模,1918年3月出生于浙江省慈溪县(今慈溪市)观城镇(观海卫镇),著名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经济学会原名誉会长。在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蒋学模一共出版学术专著30余部,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和著作10余部、文学和经济学译著10余部。其中包括连续再版十多次、印刷近2000万册的高等学校通用教材《政治经济学》。同时,他还是翻译家,是《基度山伯爵》中文版初译者。
改革开放以后,蒋学模还担任过复旦大学副校长。他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也是我们当年学习《政治经济学》的主要课本之一。因此,相对于蒋学楷,我对蒋学模了解的更多一些。他的那本二十五开本的如同砖头一样厚重的教科书我一直保存了许多年。
这样的文化斗士,学术巨匠,这样的在泱泱中华也屈指可数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他的亲孙子竟然会在陕北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的中学就职,而且还是按政策被照顾安排的。怎么回事?这其中隐藏了多少不被人知的离奇的故事?蒋俊的父亲是怎样的一个人?我的脑海里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疑问,情不自禁说道,那你爸爸怎么会来到吴堡县呢?他为什么要来这个一穷二白的山沟呢?这时候,小蒋那种自信突然没有了,躲避着我疑问的眼神,轻轻说道,我爸爸是右派!
顿时,我明白了,似乎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因为是右派,有了这个大前提,无论怎样的悲催故事都不足为奇了。
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书的蒋老师,作为文化斗士的儿子,满怀一腔热血,响应号召,给敬爱的党组织提了几条不痛不痒的意见。结果被成功引蛇出洞,刚刚结束大学生活,就顶着一顶沉重无比的右派帽子,被发配到吴堡县接受改造。这一改造就是一辈子。
春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又一次降临到陕北大地。沟沟岔岔里的柳树发芽了,鹅黄色的柳枝在春风吹拂下懒散地摇曳着。山峁上,农人们开始了新的一年的播种。那高昂的吆喝耕牛的声音,悠扬绵长,如同歌唱家在忘情的歌唱。又到了一个周末,小蒋约了我一起进城。走到半路上,他突然对我说,今天你去我家吧,我爸妈想请你到我家吃个饭。受到这样的邀请,我毫不客气地答应下来。因为我早就想看看小蒋的父亲,看看这个被日本鬼子枪杀的文化斗士的儿子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听他讲讲几十年来所受的苦难和委屈。
蒋俊家住在吴堡县城一个半山腰上。沿着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向山上走去,一直走到没路的时候,就可以看到一个整洁干净的院子,院子里有三孔大小不一的土窑洞,这就是蒋俊家。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头站在大门外远远向我们招手。毫无疑问,他就是小蒋的父亲,蒋老师。乍一见面,蒋老师和我的想象中差别很大。在未见蒋老师之前,我总以为这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经过几十年的风霜雪雨,一定是满头银发,满脸沧桑。可是,我眼前的这个老头,看上去精神抖擞,神采焕发。看见我后,远远的就把手伸过来,一边和我握手,一边问道,你就是高老师吧?我连忙说,不敢,不敢,不敢称老师,我做您的学生也不够格哪。
蒋俊的妈妈听到门外有说话声,也忙着走出来招呼我们进门说话。蒋俊的母亲一副精干的陕北妇女形象,说话做事都显得很麻利。她把我们领进窑里,看着我们在炕上坐定后说,你们先啦话,我去给咱捏扁食(饺子)。一转身就像一股风一样不见面了。
坐在蒋俊家的土窑洞里,看着眼前这个瘦小精干的南方老头,我的心里不禁五味杂陈。一个从小在黄浦江畔长大的都市青年,看惯了十里洋场的典雅时尚,来到这个贫穷落后的山沟里,娶了一个目不识丁的陕北婆姨,实在是命运多舛,造化弄人啊!
一时间,我们几个人都不说话,各自都在心里想着心事。蒋老师似乎看出了我的心里在想什么,用夹杂着上海话的吴堡话不无自豪地说,我从上海来到吴堡二十五年了,当年,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从上海来到陕北,真正是一无所有。面对这样的完全陌生的环境,生活的艰辛自不必说,最让我难以忍受的是周围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朋友,甚至没有一个可以说话的人。我多次想到了死,甚至渴望着一觉睡下去永远不再醒来。好在陕北人民不嫌弃我,把我当作先生,让我去学校教书。并且在生活上尽量照顾我,二十多年过去了,我不仅娶了婆姨,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在吴堡县城有了这么一个小小的院子,有三孔窑洞可以给全家人遮风避雨。说着,蒋老师不由分说拉着我下了炕,让我去院子里欣赏欣赏他引以自豪的窑洞和院落。
院子四四方方,虽不是很大,但收拾的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三孔窑洞是土窑洞,两孔一般大,有一孔受地势所限,比那两孔小一点。窑洞外面用石头做了一个面儿,陕北人称作接口土窑。蒋老师给我详细介绍着他的这个人生最大成就,脸上充满了满足,自豪。“高老师,你看我这个人不简单吧?我也是一个成功人士吧?”他的那种神情,让我觉得他不是在介绍他陕北吴堡的土窑洞,而是在炫耀当年上海著名的丁香花园。此时此刻,我的心里真是百感交集,人啊人,生存永远是第一位的,活下去就是胜利!假如没有那场骇人听闻的引蛇出洞运动,蒋老师也没有成为傻傻的蛇,那么,中国新闻界也许又会诞生一位大师级的文化巨匠!
不过,我感觉蒋老师还是用自己大半生的经历结结实实给我上了一课。
吃完蒋老师婆姨做的香喷喷的羊肉饺子,在蒋老师俩口和小蒋的目送下,我离开了这个蒋老师心目中的丁香花园。这一别就是四十年了,蒋老师如果在世,也应该是九十多岁的高龄了。蒋老师,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吗?
作者简介:

恺良,真名高克良,水利部黄委会黄河上中游管理局退休干部。大学学的政治教育,却更喜欢文学。
本期编辑:郝晓东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