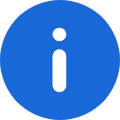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三)
在得到田自久的指点之后,我对尚居东倒也不是多么惧怕了。他安排的劳动我索性置之不理,也不去参加。他看着也无法,就只好自己领着孩子们去。
那天他领着我们班上的学生去砍柴,我却到田学全家去玩了一天。那一天田学全陪着我喝酒,划拳行令,放迷猜宝,真是尽兴,一直到晚上回到学校,才想起来要给学生们辅导自习。一见到亲爱的学生,我的头脑开始冷静下来了,我逐个地检查着他们的作业。当检查到田自花和王清秀的课桌时,发现她们两人都不在。我便问田德炎:
“自花和清秀晚上是不是没来?”
田德炎见我问他,便迟疑地回答道:“来了,做了一会儿作业,尚老师喊着给他托胳膊去了。”
我不明白地问:“托胳膊?怎样托?”
田德炎答道:“尚老师说他胳膊风湿病又犯了,用醋炒了一些麦麸子,拿毛巾包着放在胳膊上托。麦麸子一冷,就要用火烤热了再换。尚老师嫌冷,睡在铺盖窝里,叫她们两个换着给烤麦麸子。”
原来如此!我当时一股恶火“轰”地上了头顶:你尚居东白天叫我班上的学生们劳动,晚上叫给你托胳膊,这样耽搁着把学生的成绩垮下去了,又向公社汇报说我教书不行,你在我跟前用心为何如此地恶毒?我乘着酒兴,几步跨到尚居东的宿舍前,隔着门帘子喊道:
“田自花,王清秀,你们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自花和清秀到底还是慑于我是班主任的威势,迟疑了几分钟时间,还是慢腾腾地进了我的办公室。
我一见她俩那有恃无恐的样子,火气更大了:“田自花,王清秀,你们两个为什么不上晚自习?”
“尚老师叫我们给托胳膊。”田自花头一迈,抢着回答。王清秀站在旁边没出声。
“托胳膊?你们靠托胳膊能得到考试分?”我气得几乎要拍桌子了。
“那尚老师叫去,我们有啥办法?”王清秀细声地回答道。
“是的,我不是怪你们。清秀,大人把你从十几里路送到学校,为的是什么?你们两个都是十六岁的人了,在家里也能给大人帮忙喂猪,打猪草呀!但是,这些活大人都揽着做了,没指望你们,又为的是什么?你们在班上学习成绩这样落后,还不抓紧时间补起来,这样能对得起谁呢?”我一番追问,说得她们两个眼圈也红了。唉,毕竟是近成人年龄的孩子,我也批评不下去了,就给讲了一些学习的方法和技巧,说了一些如何处理劳动和学习的关系。见她们二人都很感激,就叫她们去做作业。
尚居东在我叫走田自花和王清秀之后,自然是十分的生气。我也不知他那一夜是怎样度过的,说实话,我也不想理他。第二天一早,他叫学生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我去时,他却不在,可能出外小解去了,也可能是他有意给我让开时间。我刚坐下来,一眼就瞟见他的办公桌上放着的一页纸上整齐地写着两个小方块,当时没有多思索,便拿起来细看,却是一首诗。那题头写道:
“昨日正值大雪天 气,臂上风湿病发,彻夜难眠。正是独自无聊,偶尔生感:
长 夜
长夜思绪万万千,臂患风湿胜如煎;
枕上零仃疼难忍,残灯做伴守床前。
深恨村鸡不催更,埋怨南柯飞九天;
难得晓光穿窗纱,一夜寂苦似十年。”
唉吆,这是在哪里抄得诗呀!我正在欣赏着,尚居东回来了。他笑眯眯地招呼我,我也连忙站起来让座。他见我捏着诗,便很热情地问道:
“田老师,你看咋样?”
我一时也没回答他的话,只是反问道:“尚老师,这是你写的诗?”
他噙着老板烟袋,揉了揉脸颊,含糊不清地答道:“昨晚,我胳膊疼得很,一夜没睡着。唉,长夜呀!我就以此为题,写下了这首诗。”
“你写得好嘛!”我称赞道。
他听到我的评价,当时兴奋起来,就开始解释道:“第一句是写我想东想西,想了很多;第二句我原本想写‘疼如煎’,后来又改成了‘胜如煎’,说明硬是把罪受完了;第三句我用了‘零仃’两字,第四句接着是‘残灯’作以照应,为啥说残灯,这是说明煤油灯捻子的亮被灯花盖住了都没人拨一下,我孤单的只有它给我做伴;五、六两句,因为村鸡一叫天就亮,我恨它不早些叫,催着夜里五更赶紧走过,只有埋怨自己不能入梦,这就是南柯的意思;第七句一个‘穿’字,我原来写的是‘进’字,最后一想,‘进’代表的意思慢,不符合我当时受熬煎的境况,只有‘穿’,才能说明我整夜是一直盯着窗子的,清晨透过窗纱的第一缕晓光就被我看见了,就像猛地‘穿’进来;最后一句,‘似十年’,原来写的‘一年’,我感觉还代表不了我度时如年的熬煎,所以用‘十年’一词作了归结。你看,像不像?”
“你叫我说真话?”我笑问他。
“当然,学无止境嘛!”他笑答道。
“那我就谈一点看法,”我把诗页放在桌上,也不看他,把脸转向墙就说了起来:“这首诗总体写的真实,使人如临其境,唤发起了读者对作者的同情之感。但是我认为还是太直白了一点,诗就讲究隐晦嘛!这首诗给读者的品位不够,题目是‘长夜’,开头两个字就把它拉出来了,一字没变,这在诗中是忌讳的。如果把第一句这样地改一下……”
“哼,你那样说,只能说明你读的诗太少了!”尚居东打断了我的话,一屁股坐在藤椅上,把烟袋从嘴里取了出来,在火盆腿上“梆梆……”地磕了几下。显然,他的神情极不高兴。
我只好无趣地退出,心里也有些不平:尚老师,你为什么连这几句话都不爱听,这又无损于大局呀!况且,是你叫我说的呀……
我坐在办公室,经过长时间的气闷之后才慢慢地分析到:尚居东可能从昨天晚上的火药味中嗅出了我对他不敬的味儿,这才想用文才来征服我。先写几句诗放在桌子上,叫我单独看了之后从内心发一些感慨;然后他进来听听我的赞颂之词,再教我怎样写诗填词,使我对他彻底佩服,这样好继续把我玩弄于股掌之中。谁知,我没有按他的想法上来,却说了一些与他的设计截然相反的话,这使他预期目的没有达到,感到十分地扫兴。
吃过早饭,尚居东到我的办公室。他提出今天天晴,叫学生们再拾一天柴,并说过几天下雪就拾不成了。我向他反复地说,学生和家长对这样无休止的劳动都有意见,但他就是不听。他说他是领导,一经主意拿定,就要维护声誉,不能随意改变,至于工作方面的问题,由他出面来做。他在最后还诡秘地向我笑了笑,“学校这一把火是我放的,我来收,你放心!”
放心?放个屁!家长们整天当我吵闹,我能放得下心?就这样二人说来说去,我最终还是没有附和他的意见。
……
中午,正当我在上课时,尚居东又来了。这次他立在门口喊叫我出去,我也没有理他,照常讲我的课。他在教室门口站了一会儿感到无趣,就径自进来了。这一下,我在讲台,他在讲台边,一节课来了两个老师,学生们都瞪大了眼睛瞅着我们俩。他也没待我招呼,就开口讲道:
“同学们……”
“尚老师,你等我讲结束了你再说!”我抑制着满腔的怒气,低声地拦挡他。
“你等一下,我先说!”他沉着脸,一步跨上了讲台。
如此无礼!我正是:“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一霎时,什么同志关系,什么个人前途,一切在我脑海里统统都不存在了,眼前有的只是奇耻大辱!我抓住他的领口,还没等他回过神来,就一把把他推出了门外,——不,是摔出去的!尚居东一屁股坐在三步高的石砍下,我把门“咣”地一关,回头向学生们怒吼道:
“继续上课!”
……
这一下了不得!学校出现了老师打架的事,尚居东被摔伤了不能上课!这事一时在全大队传得沸沸扬扬,很快就被中心辅导站知道了。事发的第三天,中心辅导站就根据群众反映的情况,派了尚居杨老师和田德远两人组成工作组,到我们的学校来进行调查处理。
文荣树派这两人来是有良苦用心的:尚居杨论私人关系既是尚居东的远房兄弟,又是我的启蒙老师,在公事关系上是全公社的教务主任;田德远在当着会计,是我的同族长辈,与尚居东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关系不好也不坏。这两个人来,可以说是处理我和尚居东纠纷问题的最佳人选。
住队干部孙成知道了中心辅导站派人来处理学校老师之间的纠纷,也主动地来到学校与工作组沟通情况。他并且单独找我谈话,说他们三人是公社派来的综合工作组,要我配合好处理工作,千万不敢把事情闹大。
我看着势向不好,就回家去和父亲商量,想请工作组到家里来吃一顿饭,以挽和一下局势。父亲沉默了半天,以略带自卑的口气向我说道:“咱们家里穷成这个样子,拿啥招待呢?再说,孙成是公社的武装部长,历来就看不起我们这些穷家小户的人,能把他请得动么?”
是的,父亲说的是实情。我无法子了,只好又来到学校,听任他们摆布去!
工作组的几个人既没有展开调查,也没有个别座谈了解工作情况,只是分头谝了一些闲话。那天下午把我留着没有叫回家吃饭,名义是陪着他们。这样就由贺恩贵去炒菜热酒,我们五个人都围坐在尚居东办公室的火盆边闲聊。
看看闲话扯得差不多了,尚居杨给每人发了一遍烟,把话切入了正题。他先说这次来是来看望他的哥哥和学生,接着严厉地批评了我目无师长的做法,末了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向我说道:“自智,你是我的学生,居东是我的哥,他的教龄比我还长。我能教你,他也能教你。关于你和他闹架的事,我既不想听你们摆过程,也不想说你们谁对谁错。这件事我要以老师和领导的双重身份责成你:必须无条件地向尚居东老师赔礼道歉,以取得居东老师的原谅!”
田德远接着骂了起来:“自智,你这个瞎东西,知道不知道一点轻重?居东老师和我都是称兄道弟的,你为什么不尊重?你今天能和他闹矛盾,明天还敢和我闹起来——你这不是少教么?没有二话说的,现在当着我的面,给尚老师当面认错,出钱看伤!”
二位尊长的一番指教,说得我一点都不敢犯言。坐在一旁的孙成看到火候差不多了,习惯性地“吭吭”了几声,也接着训了起来:“我看田自智,说你是少教,简直一点都没有错!尚居东是公办教师,是属于国家正式干部序列的,你能随便去打?今天敢打尚老师,明天还能打公社干部,你这作风确实是无法无天了嘛!干脆,写检讨,检讨写不深刻了再到公社去说明原因!”
孙成一番气势宏大的批评,吓得我几乎要颤抖起来——我敢到公社去么?当下只好低着头,十分委屈而胆怯地向尚居东道了歉。
尚居东不愧是老于世故的人,当时就摆出了容人的风度,很近人情地说道:“算了,算了,这事就到此为止。既然上级派二位兄弟来,我也知道个轻重。特别是孙部长在万忙当中能抽出时间来处理这事情,确实令人十分感动!二位兄弟虽然没有明说要处理这事,话说得很委婉,但我还是个明白人,难道硬要叫你们指住鼻子批评才算事?田老师刚才也承认了错误,我想,这事我也有责任,主要是在处理同志之间的领导艺术上还有欠缺。前几天我没上课,一是叫他摔得屁股有点疼,上课站不住;二是一时生气,想不开。今天在场的人都这样说了,我还有啥说的,气也消了,明天我照常上课。伤也没啥大伤,也不叫田老师出药费了,不就是买了几张伤湿止痛膏嘛!从今往后咱们重认识、重交往,我保证心里不存啥。田老师,你看呢?”
“尚老师,想不到您有这样的宽宏大量,以前的事都怪我,您大人甭见小人怪!”我从心里感动了,哽咽地说了几句,真想站起来,给敬爱的、大度的尚居东老师深深地鞠一躬。
“就这样吧,吃饭!”尚居杨作了归结。
于是,一场闹剧就在工作组的一次闲谈中化解了……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五章:矛盾时期(三)】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
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责任编辑:肖海娟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