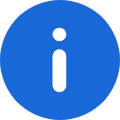这是1996年5月初的事。
学校领导关心教师们身体健康,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综合科大夫来校为大家检查身体。我被检测出有严重的心脏病,主要表现为三联律和四联率,有时还有两联率。综合科的陈主任立马给我开了住院证。
我一个教书匠,自然对医学不懂,但有必须住院的严重心脏病我却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怀疑这陈主任是为了给他们医院提升经济效益,就问她什么是三联律四联率,陈主任解释说:三联律就是心脏跳三下就停顿一下,四联率就是跳四下停顿一下。正常的心跳是匀速且不停顿的,我这种情况表示心脏随时可能“罢工”,很危险。
陈主任的解释言之凿凿,但我依然心怀猜测,于是就拿着检测的心电图,托朋友找到市医院心病科权威王大夫。王大夫看了心电图后皱起眉头,告诉我:
“人家陈主任说的是对的,是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
王大夫这样一说,我才知道我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回到学校正撞上校长,校长叫住我说:
“刘老师,我听陈主任说了,你的心瞎了,还不赶紧住院去。”
咳,这个陈主任!
没有等我说什么,校长脸色变得严肃起来,接着说:
“说是说,笑是笑,你去住院这事不能耽搁,你的课我安排别人上。”
真是一个好校长!
第二天早晨我去了附属医院,不过多了个心眼,去的是心脑病科。接待我的是心病科的曹主任,博士研究生毕业,医学教授,又有二十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多篇心病研究论文发表,应该是心病研究的权威。他仔细看了我的心电图后又对我进行了复查,而后没有丝毫迟疑的签了入院证。就这样,我开始了一个奇妙的医疗过程。
住院
医院的床位很紧张,我一开始住的是8个床位的大病房。我进去的时候两个护士正在整理床铺,说是前面的病人刚出院,重新换被单。我一看床号,66床,不错,六六大顺,是个吉祥数字。我心里一乐,护士收拾完毕之后我就急不可待的躺了上去。
说实话,我在学校带着两个文科毕业班,一个文科补习班,课程本来不轻,又在校外兼了两个补习班的课,每周正式上课25节,平均每天四节以上(那时是六天工作制),虽然教材内容是轻车熟路,但政治课嘛,每年都有新的时政内容,根据新的时政编写新的教学并非易事,加上自己有点争强好胜,所以感到挺累。这不,一躺到床上就很快迷瞪了,病房里的噪杂声一点都不影响我的睡眠。
熟睡中,忽然听到有人叫我:“刘老师,刘老师!”
我一挺身坐起来,揉揉眼睛说:“不好意思,老师迷瞪过去了。有啥问题?”
“没啥问题,是让你把氧气吸上。”
我这才注意到,站在我面前的不是学生,是穿着一身白色护士服,带着白口罩的护士,再向周围看看,这才想起自己是住在医院了。
护士把氧气瓶推了过来,要我躺好戴上氧气罩。我一听就急了,我连不舒服的感觉都都有,还吸什么氧气!
我让护士把氧气瓶推走,我不吸氧。护士说:
“刘老师,这是曹主任的医嘱,我们必须照办。”
“推走推走,我不需要。”我坚定的拒绝。
“可是,你的病很重,必须吸氧。”护士没有动,手里拿着氧气罩,好像很为难。
“什么病很重啊?我都不想来住院,好端端的吸什么氧?”我怀疑这是院方为了创收。就说护士:
“不就是为了多算一点钱吗?你在单子上签上吸氧不就行了。”
话说出去了,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再次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已经无法收回了。
护士见我这样说,就只好把氧气瓶推走了。
一会儿,另来了一个护士给我把吊瓶挂上。
看着吊瓶里的药水一滴一滴的慢慢的滴下,我无聊的开始数着液滴的点数,数着数着又迷糊过去了。
病危
“老师,老师!”
睡梦中又听到有人叫我,懵懵懂懂只看到白口罩上漂亮的眼眉,白色护士帽下乌黑的留海。
“老师,还认识我不?”口罩里传出的柔柔的声音,有点耳熟。
大概是感到我的迟疑,护士咯咯的笑起来,卸了口罩说:
“你再看看,我是谁?”
瓜子脸,弯月眉,清泉眼,秀美的鼻子下是丹红的小嘴,杨蓉,是杨蓉。
“我以为老师都把我忘了,我学习不好。”听我叫出名字,杨蓉很高兴,但语气中明显有点酸味。
我感到尴尬,不知怎样为自己辩解。幸好杨蓉自己给我台阶了。
“其实我知道你没歧视过我,你老叫我蓉蓉。”
噢,想起来了,是那个羞脸很大的蓉蓉,叫她回答问题总是红着脸结结巴巴。我知道她那一年高考没有考上,但不知道她后来成了护士。
说了几句过去的闲话后,杨蓉突然问我:“老师,师娘怎么没来陪护你?”
“你看我像个病人么?还要人陪。”我笑说。
“可曹主任说你病很严重。”这姑娘没有一点城府,直接就这样说我。
“医生就是这特点,把没病说成是有病,小病说成是大病。”
说完这些话,我突然想到蔡桓公说扁鹊的话:“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我是不是个蔡桓公?
杨蓉好像看透了我的心思,说:
“老师不要学蔡桓公,得重视这病呢。”
“好好好,我重视。”
见我这样说了,杨蓉的脸色突然凝重起来。
“老师,我给你个通知,你可别有压力。”
“什么东西呀,还会给我有压力?”我大大咧咧的问。
杨蓉给了我一张纸,我先看到的是下方盖着院方的大印,在看上面的题目,“病危通知单”,这五个字还真够害怕的。
“老师,你别担心,这也是医院推卸责任的一种手段。”
傻姑娘,现在知道安慰我了,我其实也想到了这一层。
我把病危通知单折叠好后放在衣袋里,告诉杨蓉:
“我的身体我知道,但这事你千万不要跟其他人说。”
“嗯。老师,那你安心养病,我还有事,先走了。”
“你忙你的吧,我没事。”我对杨蓉说。
杨蓉走后,我开始扫视病室。这是个大病房,八个床位上躺着八个病人,除我之外每个床都有陪护。大概是大家都知道这是心病科,说话都悄声细语的,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但看样子可能这些病人都下了病危通知单。
第二天早晨曹主任来病房,我问他:“你看我像病危的人吗?”他解释说:“你不懂心脏病,你的病很严重了,医院必须向你说明情况。”我当时就笑了,说他:“你还没给病人医治呢,就先把自己的手撕利(把责任推干净)了”他也笑了:“有这方面的意思,但你确实非常严重。”
“老师。看我给你把谁带来了?”
正胡思乱想着,杨蓉又回来了,一手提着热水瓶,一手拿着面盆,还带着一个护士,一手提着红色塑料袋,一手提着一箱牛奶,还没等我说话,她就先自我介绍了:
“我是小丽,还记着么?”
“记着呢么,我让你和王朝晖坐同桌,你不愿意还哭了呢。”我说。
小丽扭头对杨蓉说:“看,我说老师肯定记着我呢。”声音中透出得意。
“老师偏心眼,喜欢漂亮娃。”杨蓉噘着嘴好像很不满。
“露馅了吧,知道老师最爱你。”小丽反击杨蓉,不过杨蓉那时确实是班上最漂亮的姑娘。
小丽放下牛奶和塑料袋,说:
“老师,没有啥给你拿,买了几个苹果和香蕉。”
“买那干嘛呢?给你们拿回去!”
“看老师说的些,这算个啥呀?”
杨蓉把热水瓶放到床头柜上,从面盆中取出一摞纸杯,一条毛巾放到柜子里,把面盆放在我的床下,然后说:
“老师,住院用的你就不要从家拿了,需要啥给我说。”
“谢谢,不需要啥了,看把你操心的。”
“应该的,老师。”杨蓉说。
“她抄了个啥心,看这病房,人多的。”小丽说。
“这不是没办法吗?我都给护士长说过了,高干病房一有床位就把老师转过去。”杨蓉说。
“就这儿挺好的,我又不是高干。”
“看老师说的,这事你就不要管了。”小丽说我。
她俩离开之后,临床的陪护问我:
“你是老师?”
“怎么,不像吗?”我反问。
“当老师真好,学生给你把啥心都抄到了。”
留恋
开始我住的是六楼八个床位的大病房,因为学生的原因两天后转到只有两个床位的所谓“高干”病房。每天的过程都是一样,早上主治大夫来查房诊断、开药,护士按方送药、挂吊瓶,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但有两个病友让我记忆深刻难忘。
第一个是家住东乡的一个农村老太太,说是老太,也就60来岁吧,因心脏病与我同一天住院,在大病房里与我临床,有个女儿照看服侍。住院时是自己走进病房来的,与我聊天音韵朗亢,精神状态看来是颇佳的。因为是农村人,很实在,一切都听医生的,按时吃药,准时挂吊瓶,但效果却是病情越来越重,由自己上厕所到由女儿搀扶着上厕所,再到没法上厕所,躺在床上由女儿接屎尿,熬了20多天吧,老太太就去了极乐世界。我没有贬低现代科学或者医生水平的意思,事实上负责给她主治的大夫可厉害了,是从日本留学归来的研究生,当时的心病科主任,教授,后来升任为医大附院院长、博士生导师的杨大夫,在全国都有一定名气。但不管怎么说,这位老太太确实是我唯一亲眼所见的越治越重,竖着自己走进来,横着别人抬出去的病人。那个时候医患关系没有现在这么紧张,那女儿回去时还专门到我的病房向我道别,我看她泪水盈盈的,心里难受,但她一点也没有抱怨医院的意思。倒是我,心里一直对此耿耿于怀的。
第二位病人是我的一位女同事,姓杜,当时也就50来岁吧,比我晚几天住院,就住在我开始所在的那个大病房里。她这个人性格不好,夫妻关系紧张,住院的十几天里基本上都交给医院了,家里没人在身边陪护,也很少有人来探看。因为是一个学校的同事,又同病相怜吧,我每天都挤时间过去看她。
对了,我因为自觉病情不重,所以每天上午去医院检查挂针,下午回学校给学生上课。要知道,这些学生都是快进高考考场的学生了,学习特别紧张,替我上课的老师学生不满意,校长很为难。于是我主动要求把政治课都调到下午,就这样,我虽然住了43天医院,但学生的课一点都没耽搁。
那天早上我给杜老师带了一份油条豆浆早早的来到医院,哪知道在六楼心病科门口碰见个提着热水瓶的陪护,她拦住我说:“你那个同事昨晚上喊了个没停,吵得全病房的人都睡不成,把值班医生、护士都叫来了也没有用。就这都还罢了,她还屙(ba)在病房里,你进去就能闻着,把人能熏死。”
听这个陪护说了这么一长串话,我简直都没法相信。结果是一到病房门口就闻着臭气。我进去了,看见她仰卧着,两眼直勾勾的望着天花板。我叫她:“杜老师,今天的早饭是油条豆浆,赶紧吃,不要凉了。”
她没有起来,但扭过头看着我说:“刘老师,我怕活不成了!”
我说她:“嫑胡说,赶紧吃饭,我得打扫卫生了。”
我低头看她的床下,果然有一摊屎屙在报纸上,病房里的臭味当然就是从这儿来的。我赶紧把那摊屎拉出来,小心翼翼的用报纸裹好,双手捧着走进楼道的卫生间里(那时的病房没有卫生间),小心的把屎抖到大便池里,报纸塞进纸篓中,洗手后赶紧拿着拖把去拖她床下的残存屎尿,连续几次才算拖干净了。
我把地拖干净了,把她暖水瓶里剩余的热水倒在面盆里,让她洗手,然后去水房为她提水。值班的护士追上我,要我劝劝她不要大喊大叫,她们劝不了,病人骂她们。
我提水回来,看看表,8点了,医生很快就要查房了,我叮嘱她几句准备回自己的病房,想不到的是她突然拉住我的手不放,一再地说,“刘老师,我难受得很,昨晚上几次都想从这窗子上跳下去。”
说实在的,杜老师是学校教导处干事,与我平时没有什么交集,尽管我这个人爱与人说笑,但此前我们基本都没说过话。听同志们闲聊,她人不咋样,大家都不愿与她往来,她丈夫也在我们学校,姓张,两口子关系很紧张,经常打架,谁都不理谁,两个孩子在外工作也不愿意回来。这次她住院,丈夫把她送到医院后就再也没来管过她。我觉得她可怜,又是一个学校的同事,自己也与她住在同一个科室,就觉得应该尽量的帮她一下。人吗,能帮人处就帮帮,又少不了自己几个钱。谁知道十几天下来,她竟把我当做依靠了。
听她说要“跳窗子”,我连忙安慰:“千万不敢!得病了难受很正常,谁都也一样,听医生的,很快会好起来。”
她说:“你嫑安慰我了,我的病我知道,我恐怕活不了了。”
说完这话,她放开我的手,似乎是对我说,又似乎是自言自语:“我活不成了,我咋办呀!”
突然,她提高了嗓门,几乎是歇斯底里喊:“我活不成了,活不成了!”
我看到她的眼里满是恐怖,是对死的恐怖,对生的渴盼,我怎么安慰解释也都无用,她继续着:“我活不成了,我咋办呀!”声音凄厉而哀怨。她的声音招来了早饭时间给病人送饭的家属,还有病情较轻的病人涌进病房围观。医护们正在交接班,大概也是见多不怪了,倒是没有人来。
人越来越多,我怎么安慰也不起作用,她照样大喊大叫的,我实在没辙了,也就不忌讳了,大声对她说:
“好我的杜大姐呢,死就死吧,有啥咋办呀,谁都得走这条路,无非是有先有后。你前边走,我后面就来了。”
我这话大概对她刺激太大了,她当时就不说话了,只瞪着眼看着我,周围的人不看她了,也都惊讶地看我,好像我是个怪物。
见她不说话了,眼睛看着我,我声音放轻了,又重复了上面的意思:“人都是要死的,活着就是在走向死亡。医生给我也下了病危通知单。你不着急了就等着我,着急了你前头走,我后面就追来了。”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是面带微笑说的,这微笑不是装出来的,同事们都知道我爱开玩笑,这次也是当玩笑说的,不过也是实情。
我不知道她当时怎样想,反正我觉得她盯着我的眼神明显的没有恐怖了,拧过头去望着天花板,再也没说一句话。
我又安慰了她几句,然后回到我的“高干”病房,与我同住的病友是附院外二科的田主任,记得他当时对我说:“你说的话我都听到了,这话恐怕也就是你敢说。”
这话是不是只有我敢说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说那话以后,她直到死都奇怪的再也没有喊叫一声,甚至大一点的呻吟声都没有,非常平静。第二天的早晨我去医院,在护士站看到她的丈夫张老师,还有她的儿女与一些亲戚,她已经在昨天夜里悄悄的离开了人世。我和张老师打招呼,他告诉我:“老杜在昨晚走了。”听这话时,我感觉他好像如释重负。她的儿女也过来跟我打招呼,脸上有着悲切的神情。
我回到病房,心里怏怏的想:我昨天同她说的话,竟然变成了为她送行!愿她一路走好。
而我最后对她说的话,通过医生、护士的口传到学校,影响很大。我出院回到学校,好多同事就嬉笑着说我:“你把人家杜老师骗走了,你跑回来了,说话不算数。”我笑着回敬:“你们知道的,我是教政治的嘛!”
直到现在,还有老同事拿这话挤兑我,呵呵呵。
结论
以上尽说了别人的情况了,还是回头说说我自己的病吧。
我是自觉没有什么,就和曹大夫商量了,每天上午准时到医院接受各项治疗,该检查检查,该吃药吃药,该挂吊瓶挂吊瓶,下午回到学校上课,备课,就在家里吃饭。住院一个多月了,三联率、四联率没有丝毫好转,我问曹大夫,大夫回答:“病来如山倒,病好如抽丝,得慢慢来。”我说:“我这山巍然屹立,可一点也没有倒呀!”
曹大夫驳斥我说:“你还要等倒了再来呀,那跟不上了,就像你那个女同事。对了,你是想实现诺言追人家去呀!我的任务就是不能让你去追随她。”
“咳,跟你这大夫是没办法讲理了。”我无可奈何地说。
曹大夫笑了起来:“我可没有跟你不讲理,你叫田主任说。”
对了,忘记介绍了,这田主任就是和我同住一个“高干”病房的病友,附院外二科主任田耕田教授,也是附院名声在外的名医。和我一样,他也是以冠心病的原因住院的,但外表看一点症状都没有,也和我一样是上午来病房治疗,下午和晚上都不在这里,如果有急诊大病需要他,他连上午也不在病房。听到我们俩的对话,他也笑了,说:
“老曹这嘴没有个把门的。不过他说的是有道理的。你看我像个病人吗?我不也在住院。”
听田主任说完,曹大夫可得意了,他说:
“我说的没错吧,你要向我们田主任学习,既来之则安之。再说了,你的两个学生都找我了,我还得对她们有个交待。”
我无话可说了。但对自己的病就是怎么也想不通。
我住院是5月份,但四月我还上过麦积山的极顶,而且再往前,先一年去朱雀森林公园,上到极顶看冰山遗迹和云海奇观的四个人中,我是其中之一,有冠心病的人怎么可能这样?想到这些,我突发奇想,我要自己再以实践检验一下自己。
1996年的时候,附院还只有一座十二层的高楼做住院部,心病科在六楼。我就自作主张的从六楼开始爬楼梯,一直爬到楼顶,然后迅速下到地下的负一层,再马不停蹄奔上楼顶,再下到负一层,如此一口气跑了两个来回,之后浑身大汗的回到病房。
一回到病房,我立即叫负责我的住院医生检测我的心率。住院医生是刚从大学毕业不久的一位漂亮姑娘,看了我的模样大惊失色,急忙问我怎么这样了?哪里不舒服?我告诉她我好着呢,让她放心,然后说了我爬楼梯的情况。她听后就批评我说冠心病病人绝对不允许做激烈活动,我这样做会出大事的,出了事就把她害了。我笑着说她:“不是没有什么事吗?已经这样了,你先给我测测心率吧。”
“有事就跟不上了!你以后不能再这样了。”
姑娘边嘟囔着一边给我做检测,后来不说话了,脸上表现出极为惊讶的神情。我问她“怎么啦”,她不回答,只是把仪器重新检查一遍,从头又开始进行检测,一连做了十几分钟,而后才摇摇头,一副不相信的表情。
我对她的不正常反映感到惊讶,问检测结果,她回答:“你的心率正常了,怎么运动之后反倒正常了?”她告诉我,她们学的所有医学理论都是冠心病病人不能做稍微激烈的活动,活动就会加大症状,甚至为此丧命。我这种情况书上没有,她也没有听哪个老师讲过。
姑娘要我不要着急,是不是这台仪器有问题,她去另换一台。半个小时后她带着一台新的仪器回来,又给我重新检测,结果和上一个一样,一切都和前面的仪器检测的一样。
姑娘即刻向曹主任报告了我的情况,曹主任不信,很快从门诊部赶过来,并带来另一台不一样的仪器,亲自安装,亲自操作,结果一样的是眉头紧锁,连连摇头。之后说我,“你就是个怪人,这种情况闻所未闻。”但他又明确的告诉我,说我的情况还需要会诊,会诊后看看是什么问题。又叮咛我:“你不能再这样自己乱跑了,出了问题可就是了不得的大问题。”我连忙回答:“是、是。”
第二天上午,学院心脑血管疾病的最高权威,当时已经七十多岁的全国著名心脑病科专家吴春光教授,带着学院的一众心脑病科大夫、学科专家、教师,还有许多学院研究生一起来给我会诊。吴教授先用听诊器仔细听了我的心脉,之后让我连续做了100多个仰卧起坐,又做了100多个俯卧撑,然后再仔细听我的心脉。而后又用仪器检测。看了检测结果后老教授摇了摇头什么也没有说就离开了。然后那位从日本留学归来的杨主任,还有另外几个我不认识的大夫或为我把脉,或用听诊器再听心跳,不过谁也没有说话都相继离去。待所有的人都离去后,曹主任又回到病房,我问他情况,他叫我别着急,他们要开会讨论。
他们讨论的情况我不得而知,只是主管我的曹主任在间隔了一天之后到我病房来,未曾说话先露微笑,之后他告诉我了:
“你的病情诊断清楚了,想知道吗?”
我说:“你就别卖关子了,说吧。”
曹主任板起面孔一本正经地说:“会诊结果,大家一致的意见:你将来一定会死的!”
听他一说,我忍不住笑了,立即回敬他:“我对你的诊断,你不会死的!”
曹主任大笑:“我也一样嘛。你别急,听我把话说完。”顿了顿后继续说:“你死亡的原因可能多种多样,究竟死于何种原因,不得而知。”
说着,他又忍不住笑了起来。我笑骂:
“你算是狗屁权威,说了半天连个臭味都没有。”
旁边病床上的田主任也骂他:“你这家伙就没有个正经。”又回头跟我说:“曹主任就是这号货,你嫑介意,他跟其他病人可不敢这样开玩笑。”
曹主任又笑了,说:“你两个嫑着急嘛,我把结论还没说呢。”
田主任又骂他:“有屁快放,刘老师都等急了。”
曹主任不笑了,又装出一副严肃的正经:“我现在宣布会诊结果,刘老师将来会死的,死亡的原因不能确定,但绝对不会死于心脏病!”
我又被他逗笑了,骂他:“你这是个啥结论啊,照这样说你骗了我几十天,给我治的是没有心脏病的心脏病。”
他反讥讽我:“你还不满足啊?你不会死于心脏病,这是多大的医疗成果?有这结果的,你是头一个。”
笑骂完之后,他告诉我,包括吴教授在内的所有参加会诊的人谁也没有见过我这样的“怪病”,后来查找各种能够找到的资料,也没有我这种“怪病”的的记述。他最后说:“你这个怪人,让我们都多了一点见识。”
你看,不经意间,我成了医生眼中的“怪人”!这个“怪”告诉我,医生尤其是权威医生不可不信,但也不要绝对迷信。科学再发达,也有科学光芒照不到的地方。
2024年11月19日星期二
作者简介:
憨子,本名刘彦强,陕西咸阳人,高级教师,西咸作家协会会员。从事高中思想政治教育近四十年,为全国知名政治教师,曾在各类教育刊物发表教研论文180余篇,主编出版《青少年心理行为咨询》丛书、《中学思想政治课学习指导》丛书、《学习心理学》以及多种教辅读物。教学之余涉猎散文、诗歌、杂谈,有百余万字作品散见于各类报刊。退休之后笔耕不辍,编辑出版《坡刘村志》《草根憨语》等书,有《佳儿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