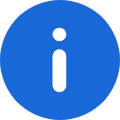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二)
我家在田家坪,和村上其他的户自然有着大同小异之处。尽管经济方面不像别人那样地过分紧张,但屋里的料理难度和左右邻舍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以前铁锤子在家时,我们家地里的活路基本上由他包了。这样有时也招来了一些闲言碎语,有的说我不在家,铁锤子借着给我们做活为名,在杨菊跟前有着非分之想。对于这些话我一直是着有着正确的分析,我相信杨菊,她不是那样的花心之人;我也相信铁锤子,他帮我们家劳动,那纯粹是站在兄弟的角度上来出力的。
铁锤子一走,杨菊只好一人当起了顶梁柱,粗细活路一齐揽。她一直拖着笨重的身子,每天起早贪黑,料理着无尽的家务。
我非常愧疚,时常觉得亏欠她的太多了。她在我们田家坪学校任教,既要教好学生,又要照顾好家庭,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辛劳。
家里常住的就是她和母亲两个人。她是一个十分孝顺的媳妇,每天一早起来到学校之前,先烧两电壶开水,中午回家吃过饭后再到院子后面山脚的水泉里担一担水。水泉距我们家约有半里路,在两颗近千年的大花栗树底,晴天倒还好,一到雨天,担着水在黄泥路上摇来摆去,有时一脚没踩稳,一下子摔倒在地,滚得满身都是泥,有几次把她摔得头发也被泥巴黏成黄疙瘩。尽管条件多么艰难,但杨菊从来没叫过苦,因为她知道叫苦也是白搭,她不可能叫我那六十多岁的老母亲去担水。
我有时回家,也很少能伸上手为她减轻一些劳累。因为我在乡上担任着副乡长,在本村是有着很大的影响力。我们村历来对于干部都很尊重,都有接干部吃饭的习惯,我每次一回家,大家以本族观念再加上对干部的敬奉,请我吃饭的人接连不断。我有时回家即使想干一些农活或家务,也常会被叔叔、婶娘或者哥兄老弟们接着陪客吃饭,天天陪着客,陪得什么事也干不成。有几次我实在是太忙了,推说不去。但杨菊在这种情况下总是对别人的行动表示支持,从来都是帮着请客的人劝我,并没有因为哪一家接自己的丈夫吃饭而有什么不悦。有两次她见劝我不听,就当着人家的面发话说:“别人请你吃饭是看得起你。人家为了请你吃一顿饭,提前准备好长时间,炒好菜,热好了酒你却不去,难道谁家还真的指望你给屙金子,尿银子?”我就这样经常地被别人邀请,同时又受杨菊的劝说,在外被吃请的多了,实在有些不好意思。杨菊也理解我的感受,为了照顾我的脸面就经常主动地向别人还人情。遇到下雨天,她就着我在屋,做豆腐,煮肉,忙活半天,炒上几个菜,叫我去接客。就这样,弄得我回家的日子基本上都是在被人请吃饭,或者在请人吃喝的日子中打发掉的。
按说,我就是给有孕的妻子帮不上什么家务,也该给她买一些滋补品什么的。但说起来简直羞煞人,我一月的工资只有三十四元钱,除开买化肥,给家里买粮,给单位交伙食,来人买烟茶招待和人情份子的开销以外,月月总是接不上,确实给她买不起什么。杨菊自从怀孕之后也不嘴馋,从来不像其他女人怀孕那样吵着要吃酸啊甜的,她的日常吃食一直是家常便饭。她怀孕十个月,总算起来我只给她买了两盒罐头,一盒是梨,一盒是两寸来长的小鱼儿。我清楚记得那天把罐头拿回家时,她板着脸把我训了一顿,说我不该拿几个工资不干正经事,她一个精壮的年轻人还要吃这些补品干啥?一顿麻达找过之后,我见她总是盯着鱼肉罐头不走眼,这才想到她不叫我买东西原来是为了顾惜家里的日子。是啊,一个孕妇,谁人真的不想吃一点稀奇东西呢?当我打开罐头之后,发现鱼肉已经变味了。而她却不管这些,拿起筷子,吃了几条,是那样地津津有味。她一面吃,一面在脸上流露出的那种甜蜜神色,使我多年以后都不能忘记……
一转眼杨菊已到了临产期。我为了弥补长时期欠下的亏债,就准备把她接到单位,这样也能使她在最需要我的时候能守候在她身边。对此,她也没有提出多少反对意见。我们给家里把柴禾攒够之后,我就给二哥二嫂们嘱咐要她们照管好母亲。就这样,杨菊还不放心,她又给我邻居的婶婶和嫂嫂们每人买了一双袜子,一遍又一遍地说了请她们每天到我们家里去看一看,叫她们多帮一帮母亲。在得到大家的一再承诺之后,她才放心地收拾了一些日常所用的东西,和我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才走到乡上。
杨菊到我们的单位后,要说我照管她还不如说她照管我。我每天一早下村,晚上才赶回单位。留下她,白天既要料理自己的生活,还要给我洗衣服,准备好开水。我则开会、下村,下村、开会,周而复始,哪有时间待在单位?哪有精力为临产的妻子洗上一两件衣服?哪里尽到一点将要当父亲的责任?
我们因为是添的第一个孩子,对产期方面的知识都不懂。问别人,有的人说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胎位正不正,并说如果胎位不顺,孩子立着下地或者横着出来,那样大人是要受罪的,有时甚至要丧命;有的则说生孩子是个简单的事,自古以来老老少少的女人生孩子,谁听说过到医院?还有的说人生人,吓死人,即使不到医院去,也应该请一个妇产科医生检查一下,自己放心……反正各种说法都有。我也不知所措,就和杨菊商量,把众人的意见综合了一下:到区上医院去显然是不可能的了,因为乡上到区上六十多里公路只有一个拖拉机通行,一个驮着大肚子的女人怎敢受得了如此的颠簸?最后还是决定请乡卫生院的妇幼专干给检查了一下。还好,妇幼专干给检查以后说胎位还正,叫我们放宽心。
那天一早,李平良给我说,县政府通知开“普六”工作会议,并说会议相当重要,把现有小学的五年制改成六年制,就问我咋办?很明显,他也是看到杨菊在这里拖着笨重的身子,怕我走不脱。按说,我是分管教育的,小学的五改六,是个大事,这个会我应该去参加。但一看到杨菊,我又犹豫了,实在是说不出要离开她的话。当下我就向李平良说,我去和向利商量,请他去开一次会。
杨菊见我为了她在身边去推会,当下就劝我说:“县上开会是大事,你应当去呀!”
我感觉很为难,但也不好当面说是因她在这里我才不去的,当下就含含糊糊地说:“开会嘛,不管谁去都是一样。”
“一样?”她有些不高兴了,“你是为了我在这里才不去开会的,这我知道。但你没有看一看,书记和乡长一天都忙得不落屋,你一个副职却在屋里守老婆,连会都不去开,这在人面子上能说得过去吗?”
“不是我不去,”我被她几句话说得很难堪,“看你现在的情况,这……”
“还‘这’,这啥呢?在家里你不放心,那还说得过去。在你们单位离卫生院几步远的路,有啥不放心的呢?”她有些不高兴了。
“不是我推辞。我们卫生院那几个医生的本事我知道,他们一年的病人差不多都跑到兽医站去了,这样的医生我能放心?”我和她据理力争。
她见我还是一味地推,就生气地说:“旧社会女人生娃谁请过医生?还不是照样生下来了?你若不去开会,我下午就回家去!”
这个犟牛!哪像个八十年代的青年人说话?我拗不过她,只好给李平良交代了一下,请他随时注意杨菊的身体状况,如果有异常,立即就去请妇幼专干来。李平良一一作了答应。当杨菊知道我叫李平良照管她时,就笑着说:
“你倒还蛮大量的呀,把一个年轻的媳妇留给别人照管,能放下心?”
我也向她笑道:“有什么不放心的?平良和我亲如兄弟,人家见你了还姐长姐短地喊,为什么不能叫她照管你呢?”
“你说得这样放心,那我生娃时就可以叫他搂腰了?”她“嘻嘻”地笑起来。
“没意见!”我也跟着笑了。
杨菊和我当时只为说了个笑话,谁知道还真按她的话上来了。
我在县上开了三天教育工作会后,接着是林特建园会,计划生育会,一家子又来了三天。我们冷水乡离县城比较远,交通又不便,县上的会议在通知到乡后,乡上就安排我把几个会接着开完。当九天的会议开完之后,我心急如焚,把自行车上绑着手电筒,骑着连夜赶回乡上。走进屋一看,李平良和李晓新他们几个年轻人正在我屋里说笑,只不见了杨菊。我心里“咯噔”一下,——莫非她到卫生院去了?
当我正要问明情况时,内室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生了!”我的第一反应一出来,也顾不得听李平良他们一片的“恭喜”声,就甩掉背包,几步冲进了内室。
杨菊安详地坐在床上,头上缠着毛巾。她见我进屋,就笑着招呼道:“你回来了。”一句话没有说完,两行泪珠顺着她的脸颊牵线似地直滚。
这时,外室传来了李平良的声音:“田乡长,开水都烧好了,你先洗一下,我们走了!”
我答应了一声,也顾不得送他们,就要去拉杨菊的手。她把铺盖揭开一角,用泪眼瞅着我说:“先看看你的儿子!”
儿子,儿子,我有儿子了!我赶忙就要去亲他,杨菊却把铺盖仍旧给娃子盖上,嗔怪地说:“刚才还在哭呢,他能经得住你亲?”
我拉着她说:“你受苦了!”
“总算没叫你失望!”她叹了一口气,“今日是娃子出生的第二天。大前天肚子开始疼,我就叫平良去请医生。谁知道卫生院的妇幼专干她妈有病,请假回家了,我也没办法,就在屋里挨着。乡上干部们都下村去了,只有朱玉分和李平良俩人,都是男人家,他们也伸不上手。请来了一个接生婆子,我一看就恶心,身上一股汗气,手上也不干净,我就干脆叫她回去了。李平良他们只能里外跑着买卫生纸、烧水,不好进屋里来帮忙的。前天到了后半夜,我疼得快要昏死过去了,这才喊他们两个进来。李平良提着我的腰,朱玉分忙着给擦洗。天快亮时,娃子下地了,是寅时的,时辰好!”
她也许是极度痛苦过了,也许是怕哭着我伤心,在说这些话时,显得很平静。既像是在讲遥远的过去,又像是下级在给上级汇报工作。
我听了,心里不由地一阵阵发酸。我原想,她在家里,只有年长的母亲一人照管,不放心才接到单位。谁知到了单位还不如在家里,她在两个外姓的男人面前,将自己的生理暴露无遗,这在一个年轻的女人来说,是多么无奈呀!而我,却在她最痛苦、最需要我的时候不能守候在她身边,不能给她一点儿安慰,却让两个男人来给她接生,我、我算个什么呀?我拉着她,只有流泪的份儿。
“哎,我想给娃起这样一个名字,你看行不?”她见我心情不好,就转移着话题。
“哟,你行。我没在家,你把娃给我生下来,还给起了名字,真是贤妻!只是不知给起了个啥名字?”
“看你说话!”她白了我一眼,“我听德教叔说过,你命里缺水,添个娃子应该起个带有水的名字,这样可以互补一下。再者,你姓田,田不能离水,就给娃子起个学源的名字。源者,寓意源泉之意,水之生根之地……”
“哈,我没在家,你倒跟上德教叔学成算命先生了!行,行,依你,依你,就叫学源!”我高兴地抱住她亲了一口。
然而,她却没有激动起来。沉思了良久,才望着我说:“自智,想办法往前走一截吧!哪怕你不要工作,我也不嫌。咱们去到交通便利一点的地方住,那样对人身的安全也是个保障。”
我点了点头。
“你看,”她拉着我的手说:“爸得了个胃穿孔,又不是多么复杂的病,但拖着时间长了就转了症,没有救转来,这在医疗条件好的地方是不会死的。你看我这次,这是天老爷保佑,娃子顺利下来了。如果再遇到个难产,你连个讯息都不知道,那你现在见到的就不是能说话的我了,你想一下,你这时候见到的……”
“别说了,别说了……”我抱着她的脸,小声地哭了起来。
她也哭了,抱着我的肩。我们俩人,哭成了一双……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二十一章:困难的日子】(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陈羽
责任编辑:刘萧娇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