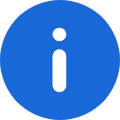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一)
从洵河县的太极城到西安的公路是沿旬河西岸而行,一直跨过秦岭。公路从洵河县址顺河上到四十公里处,又沿着伸向河心的小山岭,左拐弯直上三公里,然后又折弯与旬河成平行线上伸十公里,再顺山折一个拐然后直下到河边,再继续顺河岸直上。这一上、一平、一下使公路在这个地方折成了四个大直角,把旬河与公路之间圈成了一个巨大的簸箕形状。“簸箕”中间的十个小山岭如同人的一双巴掌叉开按在平地上,直指向河心,中间的两个“拇指”较短一些,两边的八个“指头”较长。十指岭乡就因这“十指”而得名,乡址就扎驻在两个“拇指”的交界之处。
由于地理貌形的奇特,自古以来都说这是有风脉的一块地方。从新中国成立前到如今,这里都是“公人”们办公的地点。十指岭乡人们的先祖吃苦耐劳,活跃于社会,曾在这里演出了无数曲兴兴衰衰的轶事。也许是天意安排,我人生的最大闪起点也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
人们常说:“天时有阴有晴,月亮有圆有缺;道路有山有水,仕途有闪有跌。”我多年的社会经历正应了这几句话里面所包含的哲理。我被调到十指岭乡任副书记以后,从仕途上来看职务是降了,但环境却变好了,心情舒畅了,工作也顺手了。还有更使我感到舒心的事,那就是乡上的领导们出面活动,把我儿子学源从老家转到这里的中心小学来读书。从这些方面来说,我被降职却又变成了好事。当然,这些主要得益于乡上一支精干队伍对我的促台,更重要的是得到现任乡党委书记周明旺的垂怜。
说起周明旺,他还是我在高中时的同级同学。当时他在一班,我在二班。在校时由于隔班,加之同学又多,我俩只仅仅是认识而已,根本谈不上什么熟悉。毕业以后都在农村做了几年农活,后来又一同当了农选干部,到了单位以后两个人天各一方,有时只是在区上开会能见个面,也说不上有什么交情。但我知道,我这位老同学经过多年在基层领导岗位的锻炼,处事相当稳重,对同志也是情深意长。他方脸粗眉,额前的头发畔呈“一”字形,一看就是一个杠直性子,是干事业的人。他不是立言家,但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两句话却在全区广为传说,比有些领导作的工作报告还深入人心。他的第一句话是向干部们解释啥叫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是打算自己吃亏!你如果处处想着占老百姓的便宜,为人民服务又从何谈起?”第二句话是解释怎样才能当好群众的贴心人:“老百姓找我们办事,要想到人家能看得起才来找的。给老百姓把事情没有办成,就要想到对不起人家,时时感到自己对人家有亏欠,这样群众才会真正和我们心连心!”他这两句话当时经常被其他乡的领导给干部们讲话借用着,在全区无形当中起着“语录”的作用。
他既是这样的一个人,对我当然不是完全以同学感情处事了。在我初到十指岭乡时,他就向我烧了三把火,逼着我砍了“三斧头”,使我在单位稳扎稳打地站住了脚。
他烧的第一把火,就是试探我有没有干部的素养,能不能服从于组织的安排。我当时对他的试探还没有多少思想准备,一直过了多长时间才意识到这是他的良苦用心。
那是在我报到的第二天,他到我的办公室,神情很愤慨,但语调很消沉地说道:“伙计,我也没有料到他们会把你调来和我搞搭档。他娘的,有些人把咱们这些没有后台的农村干部根本没有当个人看,用了就搂到怀里,不用了就掀到岩里!你说,你一个乡长当得好好的,现在不问青红皂白地就把你降了一级,弄来给我当助手,这不是有意在给我难堪?”
“周书记,”我见他态度很诚恳,也就接过话茬,道出了心底话:“我也想通了。咱们祖辈都是种田的人,我能有个工作,这和同龄的人相比还算是比较幸运的了。想想那些和我一同毕业,现在还一天把太阳从东背到西的人,他们现在在干啥?我在干啥?从这一方面对照来说,我还是从心底里感谢组织的。至于区上的个别人整我,没有啥说的,咱们本来就是人家手上的一颗棋子嘛!我一无钱送,二是上边没有人提携,叫人整了,也是活该!谁叫我没钱没关系的?”
“对,对!”
“你放心,我既来之,则安之,还不至于连人都认不清,绝对不会把怨气发到你的身上。你该安排什么工作照安排就是,我保证尽力而为!”
“说实话,我也是这样想的。个别瞎眼狗人整了你,咱们同学之间又没有啥隔阂!”
“是的,老同学,我感谢你能理解我。你看我最近能干一些啥工作好呢?”
“我来就是和你商量这事。”他当下神情显得有些恼火起来,“张岭是我们乡上最大的村,村上还有二十多个计划生育手术对象不到站。区上的人上半年来了五次,他们到村上去搞了个轰轰烈烈,经验总结了几十条,简报发了十几份,牛皮都要吹炸了,结果还是没有掀动一个人到站去做手术。”
“是的,区上发的简报我也看过,没想到是这个样子!”
“这个村在全区的瞎影响太大了,太瞎了!乡上的干部大部分和他们熟悉,下不了硬手。我想了想,你才到我们乡,他们又不认识,能抹得下脸来,还好搞一些。这次给你分十个硬人手,去把这件工作拿下来,也叫那些整你的人看一下,你到底是杨六郎呢还是卖麻郎,你看咋样?”
“行。啥工作都是人搞的嘛!”我也跃跃欲试。
“这个村有一个特点,”周明旺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以余延社为首的几个手术对象,每次都和计划生育工作队软磨硬抗,把全村的几十名对象结成铁板一块。现在大家都看余延社的样子,他如果去了,别人也都跟上去。”
“那就把余延社当个典型来抓嘛!”
“唉——!你不知道,”他摆了摆头,“余延社他爸和我爸在旧社会是烧香的弟兄,乡上一动手,他爸就出头来找我。现在的政策是一胎上环,二胎结扎。而他说余延社现在只有三个女子,一定要等到再添个儿子才能叫去结扎,不然的话他们余家就断了香火。就这样,每逢计划生育运动月来了,他们爷儿俩一个软磨,一个硬顶,和我死缠。缠来缠去,一缠六年,我到底拧不动他,整得我好被动。你来了,这是我当你说的底话……”
“周书记,既然是这样的情况,这次你就不要去了。给我几个小伙子,我去替你办这件事!”
“那我就先感谢你了!他妈的,以前派去的人都是躲躲闪闪,我一批评,他们还满有理由地顶我,说你书记都没办法的事,叫我们咋办?这次你去动员余延社,就不要考虑我的面情。其他的对象先从罚款入手,你去时把你原来的‘跟屁虫’小赵也带上,那个娃子机灵,防备余延社和你动手时乡上干部们不好动作……”
小赵原来是八里坪乡烟站的技术员,和我关系特别好,这次和我一同调到十指岭乡。我见周明望想的这么周到,就感动地向他作了保证:“多谢你指导。我今天晚上带人去把余延社堵在家里,叫他跑不掉。这次,我一定不会使你失望!”
“祝贺你!”他起身握了握我的手,“那你们就开始行动吧……”
我按照周明旺的吩咐,带着工作队,乘着乡上包的卡车,连夜赶到张岭村。在路上,我先给干部们说了周明旺的意见,把十几个人分成两拔。第一拨三个人,先到余延社家去动员做手术。第二拨人就坐在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作为预备队。果然如周明旺所预料的那样,第一拨人去了不久,余延社就吼天震地的骂了起来。我听到后,觉得时机已到,就带着工作队员,扑向了余延社的家。
余延社见来了这么多人,非但锐气不减,反而跳到门外,越骂越有劲。他把工作队员每个人的名字都叫了个遍,从上辈的祖宗八代一直骂到后面的几代儿孙。我见他越骂越不像话,就拦挡道:
“延社,我们是来落实政策的。叫你去做手术,有什么想法就说嘛,骂人干啥呢?”
“哟,这是哪个裤裆没有缝线的,钻出这样个怪鸡巴,我咋没见过?”余延社怪模怪样地瞅着我笑骂起来。
“甭胡说!这是新来的田书记!”武装部长拦挡道。
“这就是八里坪乡那个被人撵走的野杂种吧?你羞先人!在八里坪乡当乡长搞不了,被撵到我们这儿来当了个副书记,年轻轻的就裤裆吊扇子——走下风。哈哈……我知道你是个啥东西……”余延社接住又骂。
不提八里坪乡还好,一提起八里坪乡撵我,我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无名怒火直窜脑门,几步走到他跟前,逼着问他做手术去不去?余延社见我走到他面前,就用手指着我的脸骂道:
“呸!你狗日的还敢动手么是咋的?咱们今日就去找周明旺给评这个理……”他越骂越来劲,指头差点捣到了我脸上。
小赵实在忍不住了,抓住他领口,迎面就给了一巴掌。这一下,立竿见影,余延社的鼻子边立即现出了几个指印。也许是这一下的教训作用,他当时声音略低了一些,双手捂着脸,瞅着我含糊不清地嚷道:“你、你、你,你当领导的叫他们打人?”
小赵又来了个左右开弓,“他妈的,你做这挨打的事,长了一张挨打的嘴,都该打的么,难道还要领导使唤着才能打?”
“我跟你们拼了……”余延社扑着就要抱小赵的腿。
武装部长立在旁边,顺势拦了一脚。他本是当兵出身,余延社怎能受得了这一下?当下就来了一个狗吃屎!小赵趁势上去,一脚蹬住余延社的脖子,“他妈的,三句好话不如一马棒,乡上每次来的干部,你都要把人家的几代翻个遍!我不是乡上干部,和你一样是个农民,你能骂人我就能打人!今天是周明旺故意回避的,叫我来打你,给你狗日的说明一下,你也不要指望他来救你的驾!我今天要把你的狗头一脚踢滚,看你狗日的以后还骂人不?你说,今天做手术去不去?”
余延社的媳妇在屋里见他爬在地下不吭声,急忙扑出门外,眼泪巴巴地向我说:“田书记,你叫他们放了余延社,我去就是!”
“不行,叫他说!”我也恼怒到了极点,不依不饶。
“好我的老先人了,你说呀,我去哟……”余延社的媳妇带着哭腔劝他。
“行,行!去,去!”余延社用双手拍打着地面。
也真是怪,余延社这个多年都没做通工作的对象,在我们面前不到半个小时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当他们夫妻二人正要上车时,他的父亲听到音讯赶来了。这老汉年龄已经超过六十,说话刚劲十足。他到来后首先问乡上的书记来了没有,大家给他说周明旺到县上开会去了。老汉听了这话反倒觉得更来劲,便吼起来骂道:
“周书记没来,你们几个人球不像个狗鸡巴,倒来装啥子人呢?我今天就是不叫娃子去!”
这一下僵了!我们同行来的人都知道他和周明旺的关系,齐刷刷地立在那里,看着我咋办。我因为事先和周明旺说过底话,就劝道:
“老人家,我们是来搞工作的,你不能骂!”
“骂人咋的?难道老子还怕你?”他一跳老高。
余延社的媳妇见不是头,就急忙扑过去拦挡自己的公公,“爸,你老人家嘴上积点德,再甭骂了,这是我们自己要去的。”她婆婆也把老汉往回拉,嘴里直嚷:“我的好老先人哩!娃们都和我们分开门另开户多年了,你再甭给他们闯祸了,行不行?”一边说,一边硬推着老汉走了……
至此,余延社这个最难挖的榆木疙瘩被挖掉了!工作队抓住时机,宣传战果,立即在高音喇叭上点那些手术对象的名,限期叫他们到站做手术,交罚款。为了便利工作进展,同时公开宣传了几条政策:两天以内主动到站做手术的,乡上报销医药费、床位费、伙食费,否则,一切自理;三天以内交清罚款的,按政策规定的档次减免百分之二十,否则,加罚百分之二十。这两条政策一出,其他的手术对象一看余延社这个硬靠山已经倒了,都感到没有了依托,就积极地行动起来。这样仅一个星期的时间,张岭这个计划生育老大难村就手术和罚款达到双清。
回乡的那天下午,周明旺和马大山乡长亲自设宴为我们工作队接风。周明旺在酒会上高度赞扬了工作队的成绩,他说我们搞了一个“平型关大捷”。马大山由于以前到张岭村去过几次,被骂得没沾边,这时他见周明旺如此高的兴致,也不甘落后,索性搞了个人情做到底,他表态给每个工作队员发一百元奖金,以示鼓励。
酒会结束后,周明旺拉着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先叫马大山给我取了一条“红塔山”的烟,然后三个人又挖坑喝酒。看看他们二人都喝多了,我正庆幸自己的手气为什么这么好时,马大山笑着开了腔:
“田书记,无功不受禄,你这酒可不是好赢的呀!”
“什么意思?”我瞅着周明旺,但他却只是看着我笑。
马大山很诚恳地说:“老兄,是这么回事,朱家坡村牵高压电要从水田村接线,水田村要五万块钱接线费,每栽一根电杆窝子群众还要一千块,拉线窝子要五百块钱。你想,现在牵高压电都是群众集资的,朱家坡村咋能承受得起?为这事,两个村的群众已经闹了四、五天,我去看了一下,线杆子大部分都栽在山坡上,又没有荒他们的地,这样要钱不是属于敲诈?我批评了几个人,他们不但不听,还有几个毛小伙子差点要和我打了起来,我一看势头不对,就回来了……”
我听到这里就笑了起来,“你大乡长都没办法的事情嘛,意思是想叫我去?”
“哈哈……”周明旺大笑起来。
马大山有些不好意思起来,“田老兄,说实话,你知道我原来是个企业专干,专职管矿的,对行政的事我一窍不通。这次换届,周书记死活要搞这赶鸭子上树的事,叫我当乡长……”
“你说的不对,”周明旺笑着拦挡道:“你是区上牛书记亲自点的将嘛,我有那么大的权?”
“牛书记和马乡长原来是亲戚吗?”我来了个实话实问。
“也不是什么亲戚。”马大山也是实话实说。“今天你们俩在场,周书记是知情的,我说了也无妨。牛书记进到矿山,每次交办的事我都办好了,加之企业效益又好,我们从那以后才认识的……”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
“老兄,”马大山递给我一根烟,“两个村的群众越闹越凶,伍区长也知道了,他今天中午亲自给我打电话,叫我上手处理,两天以内给他报结果。你看这事,周书记也没时间去,我去又弄不成,现在只有请你去了。周书记说你这一向辛苦了,不好说的。因此我才出主意陪你玩两牌,叫你心情高兴了才说。你如果嫌赢的不过瘾,我再送你两百块钱,作为我私人请你的客,咋样?哈哈……”
“啥私人出钱,你以后不要欠老同学的差旅费就行了嘛!不然的话,他一月就那几个工资,下村又说好话又给别人发烟,咋能受得了?”周明旺笑着补充。
唉,这乡长倒也诚实的可爱,他用钱的方法死逼我!我见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加之周明旺又在旁边帮腔,只好答应明天就去。但我提出,要把这次带的工作队仍旧引着一路去,他俩一口答应了。
其实朱家坡村和水田村矛盾也不是多难解决的。我们工作队去了以后,把两个村的党员和干部召集到一起,宣传了县政府的政策。县政府规定:在公路、网电、电话这“三通”建设中,占用荒山的一律不予补偿;占用耕地的,视其土地等级,每亩地按三年常产的标准补偿;凡是高压电网线之间的连接,一律不交任何费用。鉴于水田村当时牵电线也是群众集资,我们经过商定,朱家坡村给补偿五千元,每个电杆窝子补偿二十元,拉线窝子补偿五元。
按照文件落实,水田村在工作中遇到了难题,有三个人闹着不按工作队的意见办,挡着不准施工。我们一商量,就以破坏“三通”和阻挠落实县政府的政策为名,和乡上的治安办联系,把这三个人带到乡上去办法制学习班——这也相当于现在搞的双轨。这三个领头的一走,其他的人还有谁愿意当这个挨枪的出头鸟?至此,牵电工程很快就完结了。
就在我们处理两个村纠纷的同时,乡上的几个人也在邻近的三台村搞选举工作。三台村顾名思义,分上、中、下三台,每个台一个组,土地也是天然的三个大零块。因为旧社会在每个台建有一个炮台,因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就以此沿袭为村名。现在上台住着李姓家族,中台住着胡姓家庭,下台住着钟姓家族。这三大家族由于都要选自己族中的人当代表,因而都互相较着劲,乡干部们去搞选举,分配的两个名额在选举时一个也没有过半,选举宣告失败。
几个去搞选举的年轻干部从来也没有经过这种事情,他们认为选不出来代表也就罢了,无非是开代表会少两个人就是。在回单位把情况汇报之后,周明旺感到事态严重,当场就责备:“这一个乡的代表名额是经过上级审定分配的,如果都像这样搞,以后人代会怎么开?第一次选举失败,还可以搞二次嘛!如果二次再选不出,才能认定这个选区代表缺额。你们这么搞,怎样向上级组织交代?”
几个干部也觉得理亏,只是一个劲地检讨。周明旺见他们也确实无法,就给我写了一个便条,叫我去补好这一课。
我接到信后,一看老同学的口气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也觉得这事非我去不可。于是就带了三个人,连夜赶到三台村。
三台村的群众虽然家族观念重,但不是不懂情理。我们去以后分别找到三个家族的代表人,讲了选举法的道理,说明了选举时必须要候选人得到半数以上票才能当选的规定。几位代表人也很通情达理,各自回去做了大量的工作。就这样,在二次选举中,我们没费多大力就把代表补选工作搞结束了。
我们回到单位时,周明旺老早就等在路口接我们了。和我一起搞选举工作的武装部长既能干,也能吹。本来选举补选工作也不是很复杂的事,而他回单位说的是如何如何地厉害,我们是如何如何地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经他这一吹,书记乡长好高兴,好佩服,又专意为我们四人办了一次洗尘的宴席。周明旺在喝酒时公开地说,区上的个别领导是瞎眼狗,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用人整人,谁没有给他们送礼就整谁。田自智到乡上时间不长,就解决了非常难办的三件大事,砍出了漂亮的三斧头。区上把他这样一个有能力的老同学乡长职务无故地撤了,他要在适当的场合问个清楚。
“真的,我非把这些事情说清不可!”他也许是喝了几盅酒,把话重复了几遍。
听了周明旺的话,我好受感动。人啊,特别是在失意之时遇到了知己,并且这知己又是自己的上级,那就会终生视作恩人。我当时感到,周明旺这样对我就正是恩人所为。他,大概就是老年人常说的命里贵人吧?
……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二十五章:阶梯】(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刘萧娇
责任编辑:肖海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