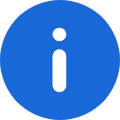九十年代中期、我参加了陕西省旬阳县的第四期农村社教作:在靠近南羊山的十里乡黑虎岩村见到一半是岩洞一半是草的独户人家共是母子二人生活,儿子年近三十生得膀大腰圆照红面庞、络思胡子,胸毛一片。主妇年过五十双鬓见白,听说我是社教作队的想让他们母子搬到庄院大队部去住,只是摇头不答,并不领情后来见我们是一片好意人也实在,便支开儿子后给我道出一段奇特遭遇:“她,曾与野人共舞!”她说:我们田家祖上三代都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到了我这辈父母只有我这一棵独苗,而且是个女子,无奈十多岁就常随父亲四处行医,上山采药。
南羊山位于陕西东南部山区,东近湖北神农架,西靠秦岭,横贯千里汉留候张良曾于此辟谷登仙:这里风景优美,是灵芝草、天麻、黄芪等名贵药材的主产地。同时,这里山大人稀,常有豺狼猎豹、野猪、狗熊等野兽出没。又听老人们讲,山上还有野人,满身红毛,力大无穷,若是抓住人,便一撕两半生吃。如果不幸碰到野人,唯一逃脱的办法就是在手腕上提前套一个竹简,若被野人抓住,野人会高兴地笑死过去,这时就可把手从竹筒里慢慢退出逃之大吉。可实际上,谁也没见过野人!
父亲年事渐高,只能在家坐诊,而在外送药,采药的活计则主要是我;父亲一再叮嘱:“采药不准进深山,送药不准摸黑赶夜路。”可那时我十七八岁,年轻气盛,偏不信邪。有一天,我起个大早,身背干粮、砍刀、挖锄、药篓等必备之物要上南羊山去采药;大约是农村吃响午饭时间,我已经上到了半山腰,一背篓草药已挖满,刚想坐下来喘口气,吃点干粮;就听见左近柴梢树叶一阵乱响,还没等我缓过神来,就见一个满身棕色毛发,眼晴发红,似熊像猿的怪兽已经窜到我的面前。转身要跑,谈何容易,前后左右不是陡崖,就是悬岩,唯一平缓的来路又被怪兽所占,情急之下,我抽出砍山刀猛然向那只即将向我扑来的怪兽砍去!谁知那怪兽只用毛呼呼的左爪一挡,砍刀便已脱手而飞。说时迟,那时快,那怪物一把抓住我的左手腕,手腕上套的竹筒被捏的四分五裂,手腕奇疼难忍,紧接着如腾云驾雾一般被怪兽拽起狂奔,一直将我拽到了一个岩洞里方才松开,那时我浑身无力,骨如散架,早已吓昏过去;也不知过子多久,一股冰凉的东西洒在我的脸上,使我悠悠醒转,就着洞口透进来的一丝亮光,模糊看那只怪物正用几片硕大的树叶也不知从哪里掬来的清水向我脸上滴洒,我用手一摸,身下铺得都是树叶和杂草倒也松软;再看身旁还放了许多苞谷穗、猕猴桃之类的野果。当时我心里一惊:“莫非真的碰到野人了!”记得老人们讲,野人会把捉到的人一撕两半生吃,顿时吓得浑身哆嗦打颤。一骨碌从地上爬起来背靠洞壁,寻找防身的家伙;可惜身无一物,也不见能拿动的石块,猛然身后一声轻响,顺手一摸,原来身上还背着一军用水壶,那里装的是用于防毒虫、毒蛇、解乏、消炎用的药酒。那野兽见我醒转便发出一阵怪笑,一把夺过酒壶,捏开盖子放在鼻前嗅了嗅便全部倒进嘴里喝得净光;我刚要趁机逃走,便被怪兽一把拽过,一阵狂舞,只转得我晕头转向,然后将我推翻在地,我认为野人怕要吃人了,立时吓得昏死过去!当我再次苏醒时,只觉下身一阵刺痛血流一地,全身的衣服被扯的稀烂;再看那野兽怕是喝了那酒的缘故,竟然酣睡在一旁,逃命要紧,我不顾浑身疼痛,摸出洞口,顾不得是沟坎还是陡崖,一阵乱钻,大约两个多时辰才跑过两道深沟、一座山梁,终于见有一独户人家,便一头闯了进去。
原来这是一户猎户人家,只有老俩口俩人生活。见我一幅惊魂失魄的样子,忙把我抬到热坑上,端来热水替我擦了脸,又熬了一碗姜汤喂我喝,问我咋回事?是不是碰见啥?这时我连惊带吓,口不能言,只用手势胡乱比划了几下便又昏睡过去,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转过来,详细向两位老人诉说了昨天的惊险遭遇。猎户大叔半信半疑,他说:“我在这一带打了几十年猎,有野猪、狗熊、豹子,至于野人嘛,只是听说,但谁也没有见过,也可你遇到的是躲进山来的走资派,你该不是看走眼了吧?
你这老不死的,看把这娃吓成这样还说东道西,亏你还是个打猎的,还不找几个人去看看!”猎户大婶是个慈样的老人,一顿数落,猎户大叔只好背上猎枪,又找了几个人根据我说的大略方位上山去了。
三天后猎户大叔回来了,找到了我遗弃在山上的药背篓,但他说:“那个山洞里象是有人住过,有一些杂草铺的窝,也有粪便和几个大脚印,可是没有看到什么野人!”几天后,猎户大叔将我送回家,父母自是千恩万谢,悲中有喜,只是以后再也不让我单独出外采药送药了。从此小小的中药铺也无法维持,更要命的是半年以后,我的肚子竟莫名其妙的一天天大起来,父亲是医生,一把脉便知就里。因为身边只有我这个独生女,从小疼爱有加,只是举了举巴掌还是舍不得打我。我母亲流着眼泪说:
“这能怪我娃吗?”
我那时年轻不懂事,也从没有与男性接触,根本不知这是咋回事,还认为肚子里长了什么瘤子。可是,左邻右舍根本不信我遭遇野人一说,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姑娘还未出嫁就怀上孩子,肯定不正经,或许是与哪个受不了批斗而逃进山里的走资派胡搞野合而怀了孩子。总之,那些闲言碎语犹如洪水猛兽扑天盖地,只酷得爱讲面子的老父亲无地自容!原与人家定的婚约也自然解除了,而且再也没有人上门看病或是说亲的,最后,随着孩子的降生,双亲双双含恨去世,在族人的帮助下草草葬了父母,我们母子无依无靠,众人骂,族人恨,我们只好四处流浪,最后还是那户猎户人家收留了我们。猎户人家的两位老人去世后,我们娘俩只能落脚在这深山老林里,一辈子不想见人,我不怪别人,只怪我命苦,才遭此说不清道不明的劫难!所以,感谢你们的好意,我娘俩就住在这山沟里,不会再到其它地方去住!
三年后,我约了几个好心人,想再去看个究竟,可村干部说,他们早已不见了踪影或许已不在人世。
(此文曾载于《太极城》杂志2004第三期《安康日报》2005年1月31日第二版)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