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三,上赵湾,
赵湾有个龙王滩,
滩上有个刘老汉,
顿顿吃饭把门关。
麻雀进去叼颗米,
一下撵了几十里;
麻雀进去叼颗盐,
一下撵了几十年。
赵湾,地处陕南旬河的上游,在旬阳市的地域划分中属于北区。民国以前交通不便,这里是西安、茅坪、旬阳和双河物产交换的集中之地,十分繁华,隔上三、五里就有私人的住宿店。那时卫生条件都比较差,住宿有害虫是免不了的,因而就有人说:赵湾的虱子——在家吃客。这可能有两重意思:一种是客人确实是受了虱子的“吃”,另一种借意是赵湾人吝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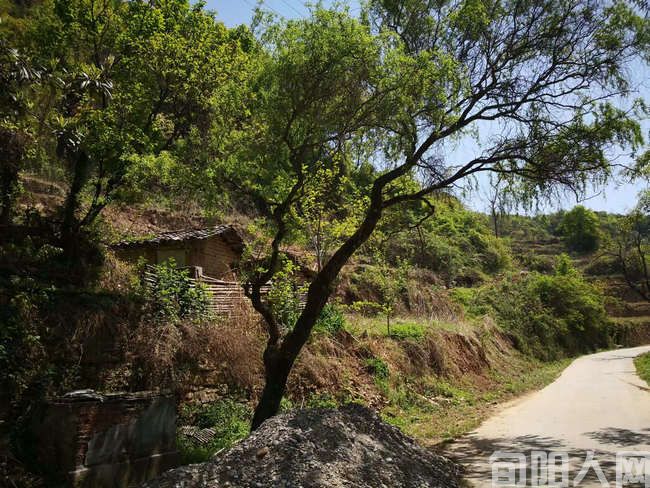
我小时候听别人唱这儿歌,说这歇后语,那时不懂事,并不知道这些话的意思。当我进入成年以后才知道,赵湾古来有各路商家过往,编段子的自然不乏其人,有一些无聊之徒编上几首损人的儿歌也不足为奇。后来在我认识了碎舅父以后,我才明白这不知道是何人的恶作为,编如此损人的段子纯粹是胡说八道!
碎舅刘桂恩,是我妻子的亲娘舅,祖辈务农,一直就住在赵湾龙王嘴的河东岸。他们那里早先是一个大院子,家家门头写有“耕读传家”、“忠孝仁义”等匾额。这里男人们厚道,女人们贤惠,为人特别客气。早先不通公路,那地方虽然偏僻但过往的行人特别多,刘家院子不管哪一户见到生熟的过路人非要留住管饭不可。在上世纪的八十年代以前大集体粮食比较缺,厚道的刘家院子人就是前门进客自己从后门出去借粮也一定不使客人们空着肚子从门前过。倘若遇到天晚,就是有再多的过路客人,院子的人也会安排住处。因此,来往的人到处传说:“古有孟尝君,今有刘家院。招徕四方客,厚道解人难!”
碎舅自小在这样的良好环境中成长,自然受到深刻的影响,忠孝行善的品德早早就在他的思想中扎下了根。到他成年以后,处事更是忠厚,急人之难,先人后己,赢得了远近人的赞颂。
我认识碎舅是在一九八三年,那时我初到信用社工作。我和妻子的关系确定以后按照当地的风俗要举行订婚仪式,其主要程序是到各亲戚家去走动,农村把这叫做“认亲”。认亲,自然是娘舅为大,我们按照父母的安排首先提着几样简单的礼品到碎舅家去。说起那次到碎舅家,唉——!拿的那几样礼品简直羞杀人,我后面还要专门说这些事。
碎舅虽居于农村,但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不平凡”,不俗气,言谈举止都有一种超脱环境的气质。我那次到他家去之后才知道,他和舅娘都是五十年代的高小生。哦,在那普遍人是文盲的年代,高小生可是秀才式的人才,比现在的研究生都少,毕业以后国家马上都要给分配正式的工作,按乡村通俗的说法就是“端铁饭碗”。碎舅和舅娘自小是青梅竹马,高中毕业正值农业大集体缺粮缺钱的时代,如果两个人都去工作家里就没劳力,没劳力就挣不来工分,没有工分就分不到粮。那是一个特别困难的年代,政策规定粮食、肉食和其他日用品都要凭票供应,不准上市交易,这样一来就是有钱也买不到糊口的东西。在环境的压抑下,碎舅家年龄大的老人干不了农活,那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碎舅是个孝子,他为了回家养活老人就果断地辞去了工作。舅娘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不但支持碎舅回家务农,在添了两个儿子之后,她眼见生活困难,也就毅然辞职回家帮助做农活养活家里的老小。
六十年代,那可是金钱奇缺的年代,人们都对拿工资的公家人是十分向往的,有谁愿意抛下轻省的职业不干而去农田里下苦?碎舅夫妇为了使家里的老人不受劳累,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双方毫不眷恋职业而回到农村,这是多么让人敬重的大孝?其精神又是何等的可贵?
由于碎舅夫妻俩都有文化,过日子精打细算,加之又能吃苦,舅娘回家不长时间就把日子过得美满幸福。都说他家是当地比较富裕的户,不愁吃,不愁穿,更不缺亲戚们送一些礼品。
我回想起来那次到碎舅家去认亲现在都觉得脸红,那拿的叫什么礼呀?我当时初参加工作月工资是二十六块钱,给碎舅送的就是饼干和罐头之类的食品,折算下来也就是十几块钱,见面简直拿不出手。但是,碎舅对我的微薄礼物并没有谈嫌,他在热情招待以后还给我们买了被面、床单、衣服和鞋子,价值要翻过我拿的礼品十几倍,我回家后父亲开玩笑说的碎舅给我“从头顶换到脚底”。当然,现在提起这些往事并不是碎舅给了东西我就小家子样地说他好,我是从这件事上看到了舅父和舅娘们轻财重义的高贵品质。每当我看到现实生活中有些人为了礼物的轻重而争执,还有的为了金钱而变相卖子女的所谓慈父慈母们,觉得他们和碎舅相比简直都是一些小人,碎舅的形象在他们面前是无比的高大!
碎舅虽然长期做农活,但并没有在艰苦的环境中沉沦,他和舅娘在做农活以外的唯一爱好就是看书。读书明志,读书明理,有志向明理路的人就有修养。尽管两人都不在工作岗位了,但一直牢记着组织上为自己安排工作的恩情,始终坚信共产党是一心为人民的,即使在交公粮、交农业税和特产税有很多人扯皮时,他家从来没有拖欠过,一直都是被评为向国家做贡献的先进户。
碎舅和舅娘正因为有良好的修养,两人的一生真正做到了举案齐眉,夫唱妇和,从来没有因小事闹过不愉快。即使在看书这一类小事方面有点意见不统一 时,两人也能用很平和的方式达到和解。
我记得碎舅和舅娘为看书发生过一次争论,现在想起来还觉得非常有趣。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全国文化界由于以前受“左”的思想影响,把一些历史名著都当作毒草作为禁书。初开始提倡改革开放时书也出的少,尤其历史四大名著是奇缺货。我当时在行政部门工作,托后门买了一些书,其中就有一套《西游记》,碎舅到我家时就非常高兴地拿着看。我见他喜欢这书,就很自然地当作了孝敬的礼物。碎舅很高兴,他知道舅娘也是个书迷,在拿回家时二人就一起分享。这一来高兴倒是高兴,却惹来了麻烦,舅娘要先看,碎舅没看完放不下。两人经过争论,最后达成和解意见:给舅娘让出几天时间不干活,白天碎舅一人上坡干农活,舅娘在家看书,晚上碎舅看书舅娘做家务活。后来舅娘当我们谝起这种和解意见时还常常忍不住发笑,那神情流露出的是无比甜蜜。我们受舅娘的感染不止是高兴,更是佩服碎舅处理家庭关系的灵活方法。不,简直是艺术啊!
碎舅不只是把家庭关系处理的好,更使人佩服的是在房屋扩建的选址方面站得高,看得远。他的老家原来在河东的河边,镇旬公路通了以后那地方就显得太背静了,他们院子的很多人想方设法把房建在公路边的地里,而他却反其道而行之,用公路边的地和别人兑换,把房建在高于公路一里多路的山坡上。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嘲笑者也有之,甚至还有人说他有神经病!面对各种议论,碎舅注意拿定,不为所动,他和大家闲谈时解释说:在公路边车来车往噪音大,离公路远一点清静。当时碎舅房子盖好以后,有些人送他一句歇后语:老刘的盖房——越偏僻越好。这,明显是贬低人嘛!
哦哦,谁也没料到天时有了轮转!不多年龙王嘴建了电站,水位上升,这一下公路边的人都要搬迁,而碎舅却是袖手稳坐。电站有一些负责安置的人们遇到事情能推就推,给搬迁户的兑现款能拖就拖。这可苦了那些搬迁的人家,他们整天找企业,有的还到政府上访,都说把腿都跑细了。这时,以前那些嘲笑过碎舅的人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无知,被他们嘲笑过得老刘是多么高明。其中有一个“聪明人”向碎舅请教:
“老刘,你是先知先觉吧?为啥提前把房建在坡上呢?”
碎舅给他解释说:“国家国家,国和家是一理。一个家庭想过好就要利用自己的资源,国家建设也是一样。公路修通了,放着旬河这么大的一股水不修电站还能搞啥?”
“那你为何知道我们盖房的地方要修电站呢?”
碎舅这才给他做了详细解释:“咱自小生长在这地方,当然对地形熟悉。龙王嘴是一条青石梁直插河心,建电站是最省工的地方了。电站不建在河洪窄的地方,谁还能挑河洪寛的地方去建吗?这窄河洪的地方就是你们原来都瞅着要建房的地方呀!”
“你那时咋不给我们点醒一下呢?”
“我又没有决定权,具体哪一年修电站我也说不清。如果当时都听我的话,那你们不是要抱怨我几十年吗?”
至此,大家都佩服了。
现在,新改建的公路直接修到了碎舅的大门口,这距他建房是二十多年了啊!二十年前,碎舅就能预料到国家现在的发展布局,自动地为基础建设让路,这正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我们不能不佩服他的知识之渊博,心胸之宽广,远见之卓识!

我的碎舅呵,真的伟大!
碎舅不但用勤劳智慧持家,而且把聪明和沉稳也传给了下一代。现在他的大儿子刘成兵是远近皆知的富裕家庭,老二刘成文是有名的专业户,老三刘成明白手起家在西安建了多年批发店以后,现在又出外包工当了老板。呵呵,这日子过的真是子贤父心宽呐!
家庭和谐,妻子贤惠,碎舅本来是很享福的,他也应该是幸福的。然而,天不遂人愿,舅娘由于操劳过度在五十多岁时离开了碎舅,这给他精神上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创伤。碎舅晚年虽然有几个儿子都争着养活,但总是难以弥补失群的伤痛。尽管如此,我的碎舅有着知情达理、忍让谦和的美德,是一个挺会着想的人。他为了减轻后人们的负担,就把对妻子的思念转到一味挂念儿女们的身上。他知道自己年事已高,在每逢生日时担心后人们受繁琐,坚持不要操办,提前就到街上的小女儿家去玩几天,平常只是在老二成文家享受着天伦之乐。
常言道:人活七十古来稀。碎舅现在已经八十多岁了,回想起来,他的拼搏历史是那样地光辉耀眼。他和舅娘本来是国家的有用人才,两人年轻时期在教育战线兢兢业业地工作,后来又在农业战线安安心心地搞生产,做到了干一行爱一行,实属忠诚敬业;他们在辞去舒适的工作后,回农村几十年如一日地供养老人,嘘寒问暖,实为真诚孝子;他们夫妻同甘共苦,终生不弃,相敬如宾,实属大义;他们能预测到国家建设的未来,几十年前就把房建在水库淹没区以外,减少了国家和个人的损失,实为大智。我能有如此忠、孝、义、智的舅父和舅娘不止是感动,更是有一种无比的骄傲!
太极城诗人鲁延河先生观至此,即赋古风诗一首,以作赞颂:
旬河上游是赵湾,赵湾有个龙王滩。
滩上刘姓居大院,地灵更有人人贤。
出类拔萃刘桂恩,不贪工作回农村。
忍让谦和处事周,目光高远屈指数。
任劳任怨敬双亲,亮节高风昭后人。
预料国家发展事,诚为忠孝又仁智。
夫唱妇和真和合,勤俭泥碗变金钵。
积德行善得好报,老来富贵乐淘淘。
更有子孙个个贤,刘氏父子美名传!
现在,碎舅已近八十岁了身体还非常健康,生活很舒心。他为了锻炼身体有时还上坡拾柴,间或到地里拔草,真正称得上别人送他的“福佬”之名。如今,在这中秋节来临之际,我以此文献给碎舅,只盼他生活幸福,盼他身体健康,盼他快乐长寿!
(二零二三年九月十八日写于西安绿地曲江名城)
作者介绍: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
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