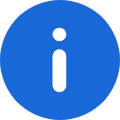距过年只有三天,突如其来的雪,拥满了山沟,世界白生生的,像母亲准备炸馃子用酵头发的面。山冈上,不时传来树枝被雪压坏的声音,声音像咒语,声音在骂着天,天不理睬那些,依然我行我素,天的脸是严肃而清冷的,一抹的铅色,人们快乐着,天没有快乐的迹象,天是要把雪下到来年吧。
村庄上空,带着香味的饮烟在高空中与雪作着较量,一个要往高处飞,一个要往低处落,它们在空中暗中拿捏着劲儿博弈,村庄就有了像被子一样灰灰的盖头。村庄里飘荡的香味,是全村人共同制造的,也是一年中少有的。我们站在村外的小河边,看着村庄上空的景致,打着赌。有人说,明天就会晴。有人说,后天太阳都不会出来。我们和山坡上被雪压坏的树枝一样,用不同的语言诅咒着天,也有人故意发了哭腔哀求道:老天呀,你能不能不再下了呀?
天不理会我们,它还是把雪片不断地向地上扔着,一片一片的,一股一股的,有时会是铺天盖地的。有小伙伴说,天太高了,我们的声音太小了,天是听不到的。我们就商量着,上到门前梁高高的山头上去,站在离天近的地方给天说话,祈求它。

我们希望天不要再下雪,不是我们不喜欢雪,是因为天再这样下雪,到了新年里,我们就不能走亲戚拜年了,拜不成年,我们就挣不到压岁钱。
正在我们准备上山时,远远地,庙岭头上有几个人影影绰绰地朝我们村庄走来,他们背着沉甸甸的东西,走路的样子像扭秧歌或跳忠字舞。有一个穿着艳红衣服的女人,不小心滑倒在雪地里,她吼唤的声音很响亮,把松树枝上的雪都叫落了。我们上山的兴致被那个女人的叫声阻止了,我们各自疯癲癲地跑回家,我们要把庙岭上来人的消息告诉家家户户正在炸馃子的大人。
在我们跑回家的当儿,天空发生了奇异的变化,一枚昏黄的太阳,从天中间的铅色云块里钻了出来,它的脸像一个慈祥的老人,带着温和的笑意,给人一种欣慰的感觉,有几束光很鲜亮地从天上斜斜地射下来,人能从那光束中看到一股顽强的力量。从天上射下来的七彩光束,有的投在山上,有的投在某户人家的屋顶上,受到光束照应的景物,富有立体感,明亮耀眼。
太阳出来了,但雪并没有因太阳出来停止飘落,依旧飘着,飘着。太阳光下的雪片,都背着一个昏黄的太阳,放射着烁烁光芒。
我关了厚重的楼门,正在家里给母亲说着庙岭上的来人,村子里传来了人们的说话声,说话声距我家近了,能分辨出是刘队长的粗声野气,刘队长经过我们家楼门时高了声腔呐喊道:公社来人,了解过年的情况了,大家都出来一下,在南头场里汇合,把各家的情况给公社的领导说说。

父亲和母亲在做饭间炸馃子,父亲把持着鼓嘟鼓嘟响着的油锅,油锅唱着快乐曲,叙说着一年的光景。父亲说,油在锅里说话,它在总结工作。母亲跪在做饭炕上,可着劲儿揉面,揉着,嘴里不停地指挥着父亲。母亲把揉好的面做成不同形状的生肖动物,放在热炕上暖十几分钟后,递给父亲,父亲将那些动物轻轻地从锅沿溜进油锅里,脸上有了笑意,他像一个指挥家,用长长的筷子,指挥着在油锅里跳舞的动物们,看着他们由白变黄,最后成为焦黄色,用于年节时待客人,父亲的油锅里向外溢着香味,香味透过门窗,和着灶膛里的烟雾飘向天际。
炸馃子一般是不会让外人进家门的,每年这个日子,村里人都在炸馃子,谁也不会轻易闯入他人家中。母亲说外人来,会带来一些不干净的东西,那样油就耗得多了,馃子也就炸不出花了。我歪着头好奇地问母亲,什么是不干净的东西?母亲撅着嘴用眼睛瞪着我没有回答。二姐见状,悄悄拉了我的手,把我叫到楼门里院墙跟,低了声神秘地重复着刚才的话,她对我说,是鬼,鬼是个瞎瞎东西,鬼进了门,油就耗散得多了。
听到了刘队长的叫喊声,二姐拉了我急着要去门外看热闹,母亲听见二姐拨门关子的声音,从炕上火急火燎地跳下来,她连鞋也没有穿,像疯了似的,扑到院子,两手抓住了我和二姐,把我们掳到做饭的屋子里,我们还在发愣,母亲找来一把剪刀,把二姐身上的棉衣用剪刀剪开一些细小的口子,接着,她把棉衣里的套子向外抽出一些,让套子在布面上吊挂着。父亲也丢开了油锅,父亲一搂将我抱到做饭炕上,他冷着脸色咬着牙很快脱掉了我身上的新衣服,让我重新穿上冬天里已经很脏很烂的破旧棉衣,父母的合作,又把我和二姐拽回到冬天里。父亲看着我和二姐的可怜样儿,会心地笑了一下,然后就让我们去听,公社的来人给村人讲什么。
雪,一片一片的下着,朦胧的太阳光笼罩下的南场里站着许多人,大部分是孩子,孩子们全穿着棉花吊在外面的旧衣服或烂衣服,前面和我一起玩的小伙伴们和我一样,刚才还在比试着谁的过年衣服好哩,这会全成了乞丐一样的人儿了。
公社来的几个人细细地看过我们每一个人,脸上都露出了苦愁的表情,那个穿着红衣服的女人一脸愁容说,刘队长,只有三十斤棉花,二百斤大米,我看就平均分了吧,天下乌鸦一般黑,谁和谁也差不到哪那儿去。
刘队长用他的小眼睛一个挨一个地看过我们,看后他微微笑了一下,他的笑有些古怪气,和他平时的笑样不是一个味儿,笑过之后,刘队长还伸手摸了几个小伙伴的头有些无奈地说,行吧,按你们的意见办。
说过,刘队长领着公社的人急匆匆地走了,在被雪深埋的山路上,公社的人又开始扭秧歌了,村人都跑到村前的小路上,看着公社的人翻过高高的庙岭,消失在雪山的那一边。
太阳还在天上挂着,天上射下来的那几束光柱不见了,太阳的光不比之前那么鲜亮了,雪还在下着,一直下着。
回到家,我问母亲,这雪要下到什么时候?母亲抬眼透过窗子吃力地看着高远的天说,你去问天吧,天知道的。
我不知道如何才能与天说上话,我对母亲说,天的架子好大呢,我曾经给他说过许多话,他一次也没有回答我。
二姐却说,天早就回答你了,是你没有听懂呢。
二姐说,天下雨、下雪、下冰雹、打雷、闪电,刮风,出太阳、出月亮、出星星、出彩虹、出各种各样的云朵,那就是天与你说话哩,是你没用心听、用心想罢了。
我想,二姐的话是对的,天没有嘴,是用行动和人说话哩。
【作者简介】:

李虎山 陕西省洛南县人,久居西安,中国作协会员,西部散文学会陕西分会主席,商洛市写作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作家,2021年、2023年陕西省主题创作、陕西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创作作家。曾于北京卫戍区服役,担任过乡镇长,报刊杂志总编。
出版长篇小说《鹿池川》《平安》《之间》,中短篇小说集《爱听音乐的狼》,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五十年的眼睛》、长篇报告文学《水润三秦》《庙岭本记》,长篇小说《平安》参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被陕西日报评为读者喜爱的作品并获蒲松龄文学奖,发表作品400万字,获各类文学创作奖50多次。
《平安》入围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之间》刚以出版,就赢得读者喜爱。
来源:为怀传统文化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