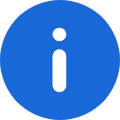季节刚将脚踩进冬天,才过农历十月一日,哑呱雪就覆盖了庙岭的山水林田路。
雪是无声无息地下,庙岭人叫那种下法是哑呱雪。
一夜间,世界改变了颜色,黑的也成了白的,白的物体增添了厚度,比如村庄外的碾盘子。世间,只有雪,才有那么大的能耐,它可以改变大自然的颜色。
下雪天,农田里的人被雪收进了房舍,村庄显得异常宁静。人们不用下地干活了,都窝在家里,烤着柴火,谝着闲梆子。
突然,两个穿军装的男人,踩着雪,嚓嚓地走进了村庄。他们头上的红五星在白雪的映照下,特别耀眼,像两颗天上的星星那么亮清。
他们最先找到刘队长。问刘队长,队上有没有人愿意当兵。刘队长没有回答他,但听明白了他们的意思,刘队长将全队人集中到社房。
人们看着两个当兵的人,许多人想起了当年抓壮丁的事。
一个年龄大的军人含着笑脸问,谁愿意去当兵。没有人回答。刘队长又把十八到二十岁几个年轻人从人群中叫了出来。他指着他们问,你们谁愿意当兵。还是没有人回答。
穿着军装的年龄大的军人,一眼看中了身强力壮的刘大谋。他把刘大谋从几个年轻人中间轻轻拉出来。问他,你愿意当兵吗。
刘大谋摇摇头退回了队伍。
刘大谋的父亲,一个留着女人发型的老汉,突然从人群中站了起来。他跳过蹲在他前面的人的身子,走到刘大谋跟前,什么话也不说,伸手向自己的儿子刘大谋,甩出一个响亮的耳光。那一瞬间,他的长头发被力气扇得从头上飞了起来。
刘大谋用手捂着脸痴愣着,浑身发抖,他用迷茫的眼睛瞪着父亲,似乎他不是自己的父亲,是当年到庙岭抓壮丁土匪的助手或者是电影里为日本人服务的汉奸。看到刘彦绪的举动,两个接兵人,迅速将刘大谋拉到自己身后保护起来。
刘大谋的父亲点着指头指着儿子的脸凶呆呆地说,日你妈的,你,不去也得去,去也得去,这是新社会,又不是旧社会,当兵是多么光荣的事。
刘大谋从两个接兵人身后钻出来,对父亲吼道,去就去,谁还不敢去。
半个月后,刘大谋被接兵人带走了,他去了辽宁,当了一名炮兵。

刘大谋是解放后,庙岭第一个当兵人。在他之前,庙岭的刘队长和张老虎,都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志愿军。
刘大谋走时,全队人为他送了礼物,鸡蛋、核桃、板栗、柿饼。
刘队长还从外队借来了锣鼓家什,公社来人为刘大谋戴了大红花。
刘大谋是新中国成立后,庙岭第一个穿上好衣服的人,也是庙岭有史以来,显得最威武的人。
雪还在下着,全队人敲打着锣鼓将刘大谋送过庙岭。
人们返回村庄时,都哭了。刘大谋的母亲哭得最为伤心。
刘大谋的父亲没有哭,他从雪地上拉起自己的女人说,儿子去当兵,又不是当土匪,你放心,会回来的。
三年后,刘大谋回来了。皮肤白得比庙岭任何一个姑娘的脸还白,庙岭人不敢相信,他还是当年那个邋遢的刘大谋?
从此,庙岭人认为,部队是好个地方,肯定有肉吃,要不,刘大谋那么瘦一个人,咋会变得那么白胖和英武。
回到家乡后,刘大谋说着庙岭人听不懂的醋溜普通话,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军装新崭崭的,军装左口袋上插了一支钢笔,笔帽上的卡子,在村人面前闪闪发光。
有一天,会计李水娃给刘大谋发什么补助,让刘大谋在表格上签字,刘大谋说,你知道的,我不识字么。
李水娃说,你不识字还插个钢笔。
刘大谋说,我想用这个钢笔给自己显花回一个媳妇。
刘大谋的父亲感觉儿子给自己丢人了。他把刘大谋口袋上那支钢笔送给我父亲,他说,让我侄子用它才合适呢。
四十多年过去了,庙岭沟垴子的人全没有了,死的死,走的走。一条沟,只剩下七十岁的刘大谋和他当年用钢笔显花回来的媳妇杨夏勤。
有一天,我见到了刘大谋。他用黑丢丢的手抓着头发说,老表呀,听说你会写书哩。
我点点头。
他笑着说,给哥一支烟。我给了他一盒烟。
他说,还记得不,我当了三年兵,挣了一支钢笔,最后给你了,你之所以能写文章,那是哥的功劳呢。你说,这一盒烟能行吗?
二次见到他时,我送了他一条烟。
我说,我送给你烟,不是感谢你的钢笔,是感谢你守着这条沟,你在着,这沟就是活的。有一天,你老了,走了,这条沟就死了。
他笑着说,那你好好给哥送烟,哥就活他个一百岁,一千岁,专门给咱守着这条沟。
其实,我知道,他并不知道一千岁是多少。
他唯一的儿子,刘军营知道。据说,他儿子刘军营,在西安城拥有一千多万元的资产。但他不喜欢西安,他说,你们住在西安,哪有这儿好么,西安城哪儿有这么好听的鸟叫么。
我们正在说话,一只喜鹊落在他的肩膀上,他伸开手,将手中金黄色的玉米粒展示给喜鹊,喜鹊叼了一粒,兴奋地飞走了。
与他分手后,他身旁核桃树上的知了们开始唱歌,声音炸得使人耳朵发麻。
刘大谋的父亲,是旧社会当过土匪的人,他一直留着清朝头,先是长辫子,后来,剪成了像女人一样的齐耳发,他是庙岭一个特殊的人,一个奇怪的人。庙岭经历了多少运动,来了多少工作组,没有一个人,要动他的头发。
记得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一年,给他们去拜年,问老人,为什么那么多运动,没有人剪掉你的头发。
他叼着长长的旱烟锅笑呵呵地说,谁知道呢,我也说不清。
后来,他对我父亲说,其实,是他儿子保住了他的头发,当年为什么要送儿子去当兵,就是想那种方法,保住自己的头发。
父亲问他,那要是儿子死在前线呢?
他静静地看了一会儿父亲的脸,然后笑着说,打仗哪有不死人的,死了,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那也是为咱们国家献出了生命、做出了贡献呀。
父亲直起腰指着他的脸说,你说得轻松的,那儿子不是你的呀。他生了父亲的气,还骂了父亲,也是从那次之后,我们再没有给他们拜过年。
我对父亲说,人家说的是道理,我们逢了好年代,我和二弟,都当了和平年代的兵,要是战争年代,那也是说不准的。
父亲想了一会儿又一次沉下脸说,看把你说得轻松的,你妈的头发咋白的,我的头发咋白的,还不是你弟兄俩个在外当兵,把我们害的。你们当兵那几年,中国和越南不是天天在打仗么,叫什么自卫反击战,我和你妈一夜一夜睡不着呀,好在你们都安全地回来了。
我说,其实,你不懂我彦绪伯,我想,他话是那样说的,他也和你们一样,放眼天下,哪有父亲不牵挂儿女的。
父亲说,那他的话咋那么硬呢?
我说,他的出身是土匪呀。
父亲说,是的,他的出身是土匪,可他从来没有害过庙岭人,他年轻时,还保护过庙岭人,所以大家都敬重他。正因为他思想转化快,让大儿子去当了兵,要不,那么多运动,早把他批斗死了。
是的,每一个人,生来都有思想,哪怕是神经有问题的人。在那些年饥荒年代,庙岭人想的是,盼望日子好过,盼望自己的儿女能活下来。
见过世面的刘彦绪,眼界有多宽,没有人知道,他用儿子当兵的事,保护了自己,他的目的达到了,多少次运动,没有人批斗过他,就像他的清朝发式,一直保持到他走向另一个世界。
庙岭人都知道刘彦绪的做法是为什么,但从来没人说破,人们不想让庙岭的任何一个人,在恓惶的日子里有什么不测。
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耳濡目染了庙岭人的所思所想和精神力度,感受了庙岭给予自己的另一种温暖。
善良,温顺,勤劳,和睦,相互帮衬,共营和谐,是庙岭人的精神追求,无论在苦难岁月,还是丰衣足食的年代,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他们看起来很土,但他们知道如何过日子,如何与人相处,如何适应形势,如何爱国,爱集体,爱家园,爱家人,爱生活,珍惜生命。
【作者简介】:

李虎山 陕西省洛南县人,久居西安,中国作协会员,西部散文学会陕西分会主席,商洛市写作学会副会长,陕西省文学艺术创作人才百人计划作家,2021年、2023年陕西省主题创作、陕西省作家协会重点作品创作作家。曾于北京卫戍区服役,担任过乡镇长,报刊杂志总编。
出版长篇小说《鹿池川》《平安》《之间》,中短篇小说集《爱听音乐的狼》,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五十年的眼睛》、长篇报告文学《水润三秦》《庙岭本记》,长篇小说《平安》参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散文集《故乡有我一棵树》被陕西日报评为读者喜爱的作品并获蒲松龄文学奖,发表作品400万字,获各类文学创作奖50多次。
《平安》入围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2019年中国明昭文学奖。《之间》刚以出版,就赢得读者喜爱。
本期编辑:肖海娟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