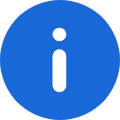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二)
我们评议小组的会议结束以后,在回家吃晚饭时,父亲见我唉声叹气,忙问我是不是病了?我说病倒是没有,就是遇到了难场事。父亲问我难在何处,我于是就把土地不好到户的事向他说了。父亲没有直接议论土地的事,只是说:
“你爷过去也是办公事的,从来没有像你一样,急得连饭都吃不下呀!”
我感到好笑,“爷爷是办国民党的事,整天向老百姓搞摊派,这与我们土地联产到劳有啥子关系呢?”
父亲也笑了起来,“说你是个外行,你还不服气。不管是啥事,总是人办的嘛!你爷爷办事很沉稳,人家首先考虑的是三条:一个是看这一件事情能办得办不得?二是看这件事办了以后缠手不?三是看这件事能办得成不?这是说……”
“您说了半天,还是解决不了现实的问题嘛!”我见父亲扯东扯西地说个不停,有些失望地拦挡起来。
父亲却耐心地说:“你甭急,我说的意见你还没懂开:你看现在把几十户的人捆在一起分地,就是心放得再公平到结果也是落个不公平,总是免不了有些人家要抱怨,说不定你这样地分,到结果还分不下去呢!我们一队去年分了五个作业组,各组之间人与土地是基本公平的。你能不能初次分地时叫他们各组先按产量划分到户,然后各组把产量一均衡,把有剩余产量再调剂给差产量的组不就得了?”
“对呀!”正是一句话提醒了迷途人,我高兴得差点跳起来,真想抱住父亲亲一下。父亲,您真的是一个才子!
平常在办一件事情结束之后,在得出结论时看起来好似很简单,很单调,但是具体在经办的过程中却是花费了千辛万苦,有时还搭上了无数的生命做代价。正如毛泽东老人家说过的一句话:“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句话看似极普通,没有“之乎者也”那样地深奥难懂,但它却是我们国家不知道好多代人流血奋战的经验总结。农村包产到户工作也是一样,它虽然不能和毛泽东老人家这么有名的论断相提并论,但事情的发展过程却都有着大同小异之处。现在农民各家种各家的地,这看起来是极简单的责任制形式,但有谁能统计得出当时在实施的过程中,基层干部们是花费了多少冤枉精力之后才办成的呢?我敢肯定,包产到户时生产队把土地分到各户的工作量,和新中国成立初期把土地从私人手里向生产队集中的难度并不会小于多少。可以说,两者都是属于土地改革的范畴!前者的办法是不管张三、李四或者王麻子,凡是私有土地统统都归于集体,不准私人再耕种;而土地包产到户时就不大一样,生产队土地原来是大家的,人人有份,你分得好了大家接受,分得不好了方案就会架在空里,无法向下落实。要想使群众真正接受你的意见,你的意见来源就必须以他们的意见为基础。正如我父亲给我说叫按作业组分地一样,他代表的是大家呼声,群众肯定也是这样想的。可以说,他这点子出得不但叫人佩服,而且是群众想说而没有场合说的,真正是恰如其分,这正是偶然里面包含着必然!
我心里的疑结解开了,吃饭也香了,看屋里的一切摆设也顺眼了,煤油灯也比往常亮一些了,房也宽敞了,我高兴地伸了伸懒腰,“啊——哟,真舒服!”
“四爸,啥事把你高兴成这个样子了?”一听声音,我就知道田学全来了。他立在门外,扶着门窗,向我笑着。
“学全来了,到屋里坐。”父亲招呼道。
学全?他是田学全?要不是他喊我四爸,要不是我父亲招呼他,我简直都认不出他来了!几个月没见面,他已经瘦得皮包骨了,眼睛深陷的有些怕人,嘴比以前也大多了,看他那整个脸型,不由地使人联想到唱戏演员们装扮妖怪时头上顶着的骷髅。
“学全,你咋瘦成这个样子了,是不是病了?”我赶忙起身拉住了他。
“没,没碍事,不要紧!”他边说边坐下来。
“学全来了,你们两个玩,你姑父来了,我去陪着坐一下。”父亲说着就起了身,他说的是要去陪田忠良的大女婿。
“爷,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田学全说着起身相送。
“算了,学全,自家人不用客气!”我又拉他坐了下来。
田学全的到来,使我几天来的愁闷一下子散去了许多。我先问他最近身体为什么闹成这样了,他长叹了一口气说:
“唉,四爸,我得下了这病恐怕不得活!”
我心里猛地一颤,像看一个陌生人似地盯了他好一会,最后才略带怨怒地说:“你咋说这话?”
“你不知道,”他语气低沉,声调悲观的像要哭,那意思好似不是说他自己,而是在叙说着与自己不相干的事。“我最近只感到左边身子麻木,可能是半身不遂。这病恐怕看不好,我也懒得治它,人一辈子总是要死的。《红楼梦》里面说得好:‘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人就是再活的高寿,最后还是要走向坟墓。”
“你这话哪儿像我们年轻人说的?有病就看!再说,我知道你也攒有几百块钱。”我几乎是吼着和他说话。
他见我动了真感情,就叹了一口气,“生死有命,富贵在天。我找算命先生算过了,我是贫贱之命。从相书上说:‘人无后脑脚无腰,枉在人世走一遭’,你看我连后脑都没有。”他说到这里,把头低到我面前,用手拍了拍后脑勺,“你们后脑勺都有个硬骨包,我这后脑勺是一抹上去,平的。你脚底有腰,我脚底连腰都没有,是一个平板;你额头宽宽的,脸上的肉很饱满;我的脸从颧骨的部位越上越大,皮紧贴着骨,没有肉。人的相貌好有一比:骨是山石肉是土,虽有石头没有土,万物不生,肯定是个贫瘠之地。再者从内相上来说,你拉的屎堆肯定像油旋子馍一样,而我……”
“算了,算了,你净是胡说一气,不说了!”我烦躁地打断了他的话。
他见我很不悦意,就转移了话题:“不说就不说了。我今天找你是另外一件事。”
“啥事?”该不会是分土地方面的事吧?这几天正为这烦着呢,我担心他说这些话。
“啥事?反正是好事!”他诡秘地笑了笑说:“是这样的:我们三队队长是他爸从王家抱养的娃,这你也清楚。他那天找到我,虽然话没有明说,但是意思却向我表达清了:你才当干部那阵,他认为你不行,没能力,有些瞧不起你。谁知道你三天两后晌就把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公社领导都看重你,你一下子在全公社红的像灯笼,连自弟叔都心甘情愿地供你使唤,他还能不佩服你?他说以前瞎了眼,没认清人,请你大人甭见小人怪,以后队上的事,只要是你安排的,哪怕是叫卖房卖瓦他都干。”
“这家伙,一天胡说八道!”我有点不好意思。
“他可能自己不好意思来说,知道我们两个关系好,就托我来替他赔情,这是他的一个想法。另外一个就是他老家有一个妹子,今年十八岁了。他说你如果不嫌弃的话,他回老家去把妹子引到他们家,请你去看一下。你如果看上了他就给做媒,保险不让你花一分钱……”
“这人也是小心眼!”我不由地笑了起来,“屁大个事,他还一直挂在心上。你给他说:我这人是宽宏大量的,从来不记刻谁,叫他放心!至于说媳妇的事,你看我目前这样子,咋提得起?房子就要倒塌,日子也过得不成式子,钱没钱路,粮也弄得不够吃。女子家里说起来不叫花钱,但人家大人把女子养那么大也费力了嘛!真的说成了,我难道连大人的一身衣裳也不给买?”
“看你说的,那能花几个钱?”
“你算一下,就是不买成品衣裳,给扯布,那也要像个样子,至少也要扯的确良布料吧?两套衣裳也得三、四十块钱呢;买彩礼认亲,少说一些,二、三十块钱也要;其他兄弟姐妹们杂七杂八地还不要个四、十五块钱?女子到我屋来,我总不可能叫她穿娘屋的旧衣裳吧?这样,一套像样的衣裳又得花三十多块钱。还有,现在提说女子都讲究三转一响(这里指的缝纫机,手表,自行车和收音机)。收音机我可以推说当时用不上,不买;缝纫机也可以给推一下,自行车也可以说当时路不通,那瞎瞎手表总是要买的。一块上海表就要一百二十多块钱,就说不买这样贵的,那杂牌的总要一个呀,这至少也需要九十多块钱。你看这几项都是必不可少的开支,总共离两百块钱也不远了。我现在的情况你知道,两百块钱我到哪里去弄呢?”
“这一门子事你放心,”田学全很轻松地笑着解释:“我还存有三百多块钱,都是这几年卖椽子挣的。你需要用时,张个嘴,甭担心!”
我见他诚心想促成这件事,就托出了心里话:“学全,我知道你是真心想给我帮忙办成这事。但是,他妹子家庭的具体情况我也不了解,女子是光脸麻脸我也没见过,咋能冒冒失失地叫人家引来看呢?如果看成了,那倒还好;看不成,那不是给女子留了个瞎名誉,别人还会说人家没人要?再说,还不知道女子念过书没有呢,我总不可能说一个文盲媳妇吧?”
“那倒也是。”他很理解地说:“女子到她哥家来过,我也看见过,胖胖的,白白的,圆圆的脸,大眼睛,就是牙有点向外龇,这在相书上叫露齿。唉,看我又扯远了,反正不算顶漂亮,也不算丑,人才是个中等。至于文化方面,我倒也没有问。这样吧,我再打听一下,等情况弄清楚了,你再去看,咋样?”
“好嘛,时间也不早了,我们洗澡睡吧!”我说着起身拿着电壶去倒水。
“我不洗,我在屋里洗过了的。”他也起身到厨房去给我舀凉水。
我端着脸盆,坐在门外,刚拿起毛巾要洗,就见田学全出来拦挡道:“四爸,外头有风,小心感冒了,你还是到屋里去洗!”
“不要紧!”我边擦着身子边说:“外头凉快,我有时都在外头洗冷水澡呢!”
我当时没听田学全的话,在门外迎着风洗完了澡。谁知,不听良言相劝,很快就招来了祸!第二天,我只觉得脑心不停地跳着生疼,眼也胀,鼻子也呛,喉咙也干,浑身软困无力。我知道,这是重感冒了。田学全急忙去弄药,我们评议组的人也轮番来问候。
我这一病,一队轰轰烈烈的联产到劳工作自然就停下来了。田德印见我一整天没有召集开会,来到我们家里问我时,才知道我病了。他和我啰啰唆唆地扯了一会儿闲话,就特意回家提着一块腊肉,十斤重的一壶酒,还有两升大米来看我。
农村一般给干部送礼都是晚上去,这原因很简单,就是怕旁人议论时说你舔沟子(舔沟子:农村把那些丧失人格、不择手段巴结人的行为叫舔沟子)。晚上送礼,干部们一般推说提前没有准备,很少给送礼的人做饭吃。这样一来既得了实惠,也省去了很多的麻烦。送礼者当然也不图吃这一顿饭,他们只图办事,并且办了之后不落啥瞎名誉。干部不管饭刚好,他们可以在这互相客套的推让中把自己的要求提出来,一般能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田德印这次名义上是来看我,实际也是为了送礼。他这次送礼时间也选的很特别,专意挑人们做活回来吃饭的时间,提着几样东西,大有招摇过市之势。他在见到人时还故意和人家闲扯几句家常,好使别人知道是给我送东西的。当他快到我们家时,遇到了田自文。田自文见他提着酒,就好奇地问:
“德印叔,今日到哪儿去呢,送这么重的礼?”
田德印故意大声的说:“这两天忙得要死,谁还顾得上串亲戚?自智病了,你看我们这是亲门子,他就和我自家的娃们一样嘛,我去看一下子……”
我在屋里听到他说这样的话,当时就感觉很不好意思:我一个年轻娃子感冒,又不是个啥了不起的事,还劳别人来看望。况且,来看我的人又是自己的亲族长辈,这叫人如何受得起?话说回来,德印叔也是怪,你是长辈,来看看我是可以的,还拿一些东西干啥呢?就是要给我拿一点啥,也该到晚上的时间再来嘛,为啥还要挑吃饭人多时鲜明张张地来呢?你,你咋能把给晚辈送礼当牌子耍呢……
田德印给我送礼的动机我难以评论,但从良心上讲,他那次送礼,从现实生活上来说确实是给我帮了大忙。自他那次送礼过后,其他人受到了感召,我们家那几天来送包包担担的人往来不绝。先是评议组的几个人来,继之是亲族中人,后来竟然发展成全队普遍性的了!开始时人们一般晚上来,到后来也就没有人顾忌这些事了,不但是白天来送,而且还约上一帮子人一起。我从他们交谈中得知,这些都是在为我着想,因为我目前又没说下媳妇,做饭全靠一个老母亲,晚上来了,老人家做饭难熬夜,单独来一个人送礼我家一天做饭没顿数,不如白天多约上几个人一起来,这样我们家里做饭也省事,他们还能和我聊一些事情,领会一些政策。我闲下来一算,全队的人基本上都来了,而且越到后来人送的礼越重,像三队的队长和会计这爷儿两个,他们把自己在山上打到的两百多斤重野猪给我分了一半,我们一时吃不完,只好用盐腌了晒肉干。这种公然的举动,带动了那些还在观望的人,使一些人感到如果不趁这个机会给我送礼,好像在人面子上说话抬不起头似的!
我的几天感冒,给家里带来的进项是近几年来未有的:大米收了两百多斤,猪肉比我们喂两年的猪肉还多,麦子也够吃几年,酒多了没处装,只好向别人借了两个坛子。收了几十条子烟,最差也是一元八角钱一条的“宝成”牌,还有几条两元七角钱的假长支“七里香”烟。最值得一提是:三队从集体的公益金中提取了二百元钱给我,名义上是说叫我办公用,实际也没开什么收条。两位干部都很清楚:他们的业务往来主要是从我手上过,大队审核,公章要由我给盖,大队长的章子,难道我这个当兄弟的还要不来?这两百块钱和众多的酒肉,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家生活窘迫的局面,从事实上给我帮忙支撑起了门户。以前公社干部来,我们要管饭时啥都没有,米和酒都要东挪西借,烟茶大部分要到代销店去赊。现在好了,公社就是一次来十个八个人我也能管得起,啥都不向别人借!我不但把代销店赊的账一次性结清了,而且还新买了被单和被套,新置了大小桌和椅子。这一下客人们来到我们家时,坐新的,睡新的。要抽好烟,我有;要喝好酒,我也有;要喝好茶,我还是有;想要吃野味肉了,我什么都不缺……孙成那个平常走路朝天看的家伙,原先在我家吃一顿饭就好像给我多大面子似的,喝酒时想起啥时训我就啥时训。现在来了真正比亲弟兄还亲,见了我母亲也一改往日白搭话的习惯,亲热地喊起了“婶子”,有时还顺便给捎买一斤七角钱的白糖。我自然也不好记刻他什么,每天在管足了他的吃喝之后,还甩给他一包烟。当看到他那受宠若惊的感激神情时,我心里不由地升起了一种施舍人的满足感。哼,当个干部到底比不当啥强,屋里有东西了谁都能看得起,日子过好了谁都会耍牌子!人头上长有毛,谁还会故意去装秃子?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八章:联产到劳的时候】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
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责任编辑:肖海娟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