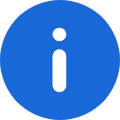(三)
我父亲曾向我们说过:人一辈子,有时费尽艰辛努力得来的东西,却不知道珍惜,只有在这些东西失去了以后,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珍贵价值。是的,父亲说的这是至理名言,我到八里坪乡当乡长的工作经历就证实了这一点。
八里坪乡是一个两千八百多人口的小乡,共计八个村。这样一个乡,区上给配的干部却够数:共计十七个人,折合起来两个人包一个村,在乡上还能留一个办公的。乡干部平均每人没有管到一百六十个人,要细算起来,还没有一个中等村民小组的组长管的人数多。总的乡情是山大人稀无来钱路,农民收入的主要支柱靠粮食。
这样的乡情,干部和群众又是这样的比例,干部工作就是想飘浮也“浮”不起来,从领导到一般同志不管搞什么工作,自然都是一竿子插到底。
乡党委书记尤立忠,我们在社教时就听向利国经常喊他是“年轻的老同志”。说他是老同志,其实不假,年龄已经近五十岁了。说他年轻,也能沾上边,因为只有三年工龄。他原是柳树乡所在地的村主任,调到八里坪乡上只干三年就被提拔成了乡党委书记。
说起他的提升,还真的带有一些传奇色彩:原来区上的领导都联挂着乡,柳树乡在全区最大,自然由区委书记罗进步挂联。柳树乡的人最难管理,也是全区出了名的。当时区上干部形容几个乡的人时曾一种说法:难管的是柳树乡,听话的是八里坪;摆摊挣钱是洵湾,能说能干十指岭。柳树乡的很多人不注重发展产业,育龄妇女超生的也多。他们在对付计划生育工作的干部时,主要方法就是一吵,二打,三躲避。一部分人在对付动员栽烤烟的干部时更有绝招,开始时说下烟苗没有技术,干部只好领着烟草技术员去把苗田整好,又把烟种给撒上。但是在烟苗出来的时候,他们却到夜里担两桶开水往烟苗上一泼,第二天把干部叫到当面,说自己的烟苗得了症,骂烟草技术员把自己的地整糟蹋了,结果仍然种自己的庄稼。干部们没办法,只好又给买烟苗,帮助把烟给栽上,他们当晚又偷着搞“拔苗助长”,第二天烟苗子死了,又骂干部们不会栽烟,最后还是照样种自己的地。可怜柳树乡的干部,为着那百分之二十一的烟草税(烟草税:本来烟草的税收是百分之三十一,区上抽出了百分之十),被农民骂得不如龟孙子!
尤立忠在当村干部时候,对付老百姓的这一套很有办法。他对那些计划生育手术对象,带人强拉着到计划生育服务站去上手术台;对不栽烟的户,在麦子将要出穗时,他掮着梨,吆着牛,去把绿油油的麦子犁成麦苗和土地成三比二的条带,然后强迫着叫栽烟。他不管农民有没有烟苗,少完成一亩栽烟的任务硬要收取一百六十元的罚款。这个罚款数是按一亩烟草能收八百元钱的最低收入,用收入乘以税率算出来的,谁不害怕!
尤立忠的这一套做法被罗进步看中了,立即就在全区进行推广。全区很快就掀起了小麦开带的热潮,一年栽烤烟就有一万多亩,比上年增长了一倍还多!自然,罗进步也没有亏待尤立忠,把他一步提到八里坪乡当了农选干部,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两年后,正式当上了书记。
尤立忠的工作既然是这样的强硬派,又是坐“直升机”提起来的,为人处世自然是目空一切了。区上安排我与这样的人搭帮,无论是年龄上还是从文化和性格上,都是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我被调到八里坪乡工作,在第一次开会时就和他吵了起来。
那天中午召集乡干部们开会,天还有些冷。干部们都到了会议室,而尤立忠却还迟迟不到会。我望着几个空落落的火盆,看着乡干部们一个个冻得颤抖的样子,就对办公室文书说:“你去拿铁锨铲一些木炭来,每个火盆加一些,把火生着嘛!”
文书没有动,望着我,只是笑。
看他如此模样,我以为他是懒去的。因为会议室到保管室隔着一个场院,还有九层石梯坎。我当时有些愠怒,就追问了一句:“你咋不去?”
他仍是笑。
这时,坐在一旁的副书记钱玉安搭腔了:“保管室的钥匙在尤书记手上。”
我不好说什么,还以为尤立忠临时把钥匙拿着干什么去了。这时,只见尤立忠端着一铁锨炭,给每个火盆里分了一点,又折转身铲炭去了。
看着乡干部一个个谈得嘻嘻哈哈,而一个书记,又是许大年纪,这样拿着铁锨跑出跑进的实在有失尊卑。当时就劝道:
“尤书记,你歇一会儿,叫文书去铲嘛!”
“保管室的钥匙我拿着,我不放心他们!”尤立忠立在门口,回头对我说:“他们也不知道俭省,一次铲一大火盆。乡上买的几百斤炭,不够他们三天两后晌就烧完了!”
原来如此!我笑了起来,“给他们说一下,叫每次少铲一些嘛。看你那么大的年纪,又是领导,这样跑出跑进的劳累,我们一些年轻同志在这里坐着也不好看呀!”
“你嫌不好看就不会不看?”尤立忠高声地嚷叫起来,脸色黑的吓人,“你们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勤俭过日子,一天大手大脚的,谁给你们挣得钱?你才到单位几天时间,挣了几个钱?有什么资格嫌我不好看?”
“你这人,我是好心劝你嘛!你不懂话是不是?”我在这众多的干部面前受不了他的抢白,就回敬了他几句。
“谁不懂话?我快五十岁的人了,咋地不懂话?还要你来指教?你才是几天的个娃娃子?”他索性不去铲炭了,舞着手和我吵了起来,把铁锨在地下蹲得“喳喳”直响。
“你摆啥老资格?我说了那样一句话,就把你的嗓子给冲了?”我也立了起来。
钱玉安急忙一把拉住了我,“算了,算了,不要说了!”他见乡干部们这样围着看热闹也确实不像话,就向大家挥挥手说:“都先休息一会儿,会议放到下午再开!”
乡干部们见两个领导吵架,坐在当场都觉得不知所措。钱玉安一张口叫他们休息,就争先恐后地跑出了会议室。至此,我到乡上开的第一次工作会议,就这样地一吵而散。
钱玉安没有走。他在会议室拉住我一直没有松手,生怕我年轻气盛,做出什么冲动的事来。这些,我当时还没有多少感受,事后想起来,还真要感谢这位比我大几岁的好哥哥。要不是他拉我,我不定真的能冲出去和尤立忠好好地干一仗!这老家伙,实在是欺人太甚!
当下钱玉安拉着我到了他的办公室。他先给我倒了一杯水,又和我扯了一些闲话,待我情绪稳定下来之后,他才把乡上的情况向我说了个详细:
“老弟,你和他有个啥争的?他就是那样个人,家长作风搞惯了的!乡上啥事都要他说了算,大小事情都要经过他的手,原来的乡长就是叫他搅得搞不成了人家才申请调走的。我是个阿弥陀佛的人,他叫干啥就干啥。我抱住一条,不贪权,把本职党务工作搞好就行了,所以他对我还好,也不整我……这次换届调你来,给你配的那个副手刘小芳,她娘家还是你们冷水乡的,婆家在八里坪。在政社分设时就调到这里来了,你们原来认识吧?”
“认识。她原来在公社时当着计划生育专干,我还在当大队会计,没想到她现在能当上副乡长!”我摇了摇头。
钱玉安笑了起来,“老弟,听你这语气还有些看不起她的意思,人家还看不起你呢!”
我也笑了,“钱书记,你不知道,她原来在公社就是跑闲路的,也办不了啥硬事。说实话,她有多大的能力我也清楚,有什么看不起我的呢?”
“你不知内情,”钱玉安一本正经地道开了:“尤立忠到我们乡上一年多的时间,还是他当书记前的那阵子吧,刘小芳从长远着眼,就叫她的娃子把他拜成干爸。两人下村都要走到一路,讨厌得很!现在老尤推荐把她当上了副乡长,在你们分工时又叫她分管财政工作,你想过你的处境么?”
“经常想。”我老老实实地承认。
“刘小芳背过你的面就到处散布说:‘田自智原来是一个经常掮椽子卖的人,我当公社干部时他还是大队上的一个小卒子会计,有什么能力当乡长的?根本没有资格来领导我们的……’她这一说,尤立忠自然就看不起你了,所以他才能当着那么多的乡干部面,说你是个几天的娃娃子……”
“那你说我以后咋办呢?”我虚心地请教他。
“我们目前的工作重点是财政和农民的增收问题,这两样搞好了,工作就上去了。至于乡上的其他事务也没有个啥了不得,财政方面一年仅仅收入六万多块钱,干部工资一季度能发一次就不错了,也没有其他的收入,他们两个人要管了也好,你肩上的担子还轻快。我想,只要你做出成绩了,区上的领导该不会把眼睛长到后脑勺上去吧?”
是的,钱玉安说的是苦口良言。小小的一个乡,有什么权不权的,争什么呢?我还是要干出一点事情,叫区上的领导们看看!
主意拿定之后,乡上内部管理的事我也就很少插手,尽放着叫刘小芳去管。我一门心思地把烟草工作安排好以后,又蹲在朱家沟,抓扩大黄姜面积的工作。当时,黄姜在全县还是个冷门,我抓的朱家沟村黄姜规范种植点,很快就引起了县上领导的重视。县上的领导们正为财政收入没有新的增长点而发愁,他们在八里坪乡检查工作时见到黄姜栽植点,立时就来了兴趣。几个领导看了以后回到县上,在很短时间里就带领全县的财税干部到朱家沟村参观,这样很快就在全县掀起了种植黄姜的热潮。只三年时间,全县就种植了二十多万亩。我们八里坪乡的农民在卖黄姜种时可发了大财。随着农民增收,乡上的财政收入也上去了,第三年就达到三十多万元,在我任届期内增长了四倍。这一下事情也好办了,我们一鼓作气,接通了十二公里的网电,使有史以来,高压电照明第一次进入了各农户。
八里坪乡的面貌,经过我们三年的努力改观,已经是焕然一新了!
【选自长篇小说《变迁》第二十四章:第三次起落】(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任登庚,男,汉族,大专文化程度,共产党员,出生于1960年11月,家住旬阳市白柳镇佛洞村。安康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作家协会会员,旬阳市人文学会会员,旬阳市老促学会会员,在四级调研员岗位上退休。1978年高中毕业后,历任代理教师、大队会计、信用社信贷员。1984年任副乡长,从此在乡镇历任乡长、党委书记、人大主席,期间参加党校在职函授学习两年,离职在党校学习一年,在职参加《清明》《希望》小说函授学习两年。回县级单位工作后,历任正科级纪检组长、副局长、四级调研员。平时爱好文学,公开出版三部书,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变迁》。
本期编辑:刘萧娇
责任编辑:肖海娟


免责声明:本站部分图文、视频、音频等资料来自互联网,如果您发现本网站上有侵犯您的合法权益的内容,请联系我们,本网站将立即予以删除! 版权所有 © 今日瞭望网(www.jrlw.net) ICP备案/许可证号:陕ICP备2023000076号
人物专访问,发稿宣传:19891525369